译者按
本文选自王浩最后一本著作A Logical Journey—From Gödel to Philosophy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6)的引言部分,有删节,题目为译者所加。
众所周知,虽然Solomon Feferman等人编辑的哥德尔《文集》已经出版了4卷,但哥德尔大量的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至今还隐藏在书信和私人淡话中。王浩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是整理他在70年代与哥德尔的谈话,连贯一致地报道和解释哥德尔的哲学观点,另一个目的是利用这些材料阐述王浩自己的哲学信念。书中内容包括哥德尔的生平与思想发展,他对上帝和来生的玄思,他与王浩谈话的背景与内容,他对于不同的哲学和哲学家的议沦,他证明心比脑和计算机优越的企图,他关于哲学作为精确科学的设想,他对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的论正和建立公理形而上学的尝试,以及他试图发展一种作为概念论的大逻辑的理想。
这里节译的“引言”部分,是全书概要,一方面简述了上面这些内容的要点(当然有些要点在这里未能、也无须充分展开),另一方面在作者所构想的哲学框架内,对哥德尔表面上零散的思想做了梳理和评价,说明它们既与西方哲学主干密切衔接、又远超时代潮流。虽然哥德尔的宏大规划并未完成,但其方法的新颖与内容的深刻,无疑为当代哲学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最后,王浩谈了他自己对于哲学、数学和逻辑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并借助清晰性和确定性标准,试图为不同的数学和哲学建立了一种由弱到强的谱系,使得我们在解释上能够消泯其中的抵牾,达成一种“公意”的统一一下浩建议,我们应该用这种方法来理解和接受哥德尔哲学的深浅不同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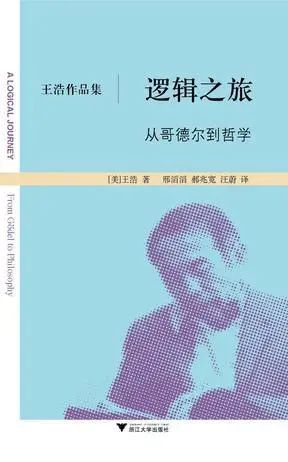
《逻辑之旅:从哥德尔到哲学》(A Logical Journey—From Gödel to Philosophy)于2009年出版。
撰文 | 王浩
翻译 | 邢滔滔01
哥德尔其人及其定理
库尔特·(弗里德里希)·哥德尔(Kurt Gödel,1906-1978)是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逻辑学家。1951年2月,哥德尔卧病在床,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告诉临床医生:“你的病人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大的逻辑学家。”在1978年3月3日的追悼会上,韦伊(André Weil)认为,承认哥德尔是2500年间唯一能不带夸耀地说“亚里士多德和我”的人,其实是平淡无奇的。
70年代,惠勒(John Wheeler)说道:“如果你称他为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你是在贬低他。”哥德尔自己倒觉得最适合与莱布尼茨为伍。不管怎样,没有人否认他在逻辑学家中的地位相当于爱因斯坦在物理学家中的地位。
爱因斯坦从1942年起直到1955年去世,与哥德尔过从甚密,他本人认为哥德尔的工作对数学,与他的工作对物理学,有同等的重要性:“既然我遇到了哥德尔,我知道数学中确实存在同样的东西。”[1]哥德尔的工作是现代逻辑中的一场革命,从数学和哲学上大大提升了现代逻辑的意义。
另外,在他的手里,数学和哲学意蕴丰富,优美异常,且无半点门户怨气。在意见相左的思想圈子中,他享受如此的尊重,为当世所少见。世人相争相斗,乐此不疲,他却超然于竞争之外。他的著作,对当代逻辑的所有分支来说,都是基础和生命力。在哲学中,情形却相反,他大量的著述还未发表,对他的观点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52年6月17日,哈佛大学授予哥德尔名誉博士学位,称他是“本世纪最有意义的数学真理的发现者。”哥德尔在给母亲的信(7月22日)中,说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这个评价“毫无疑问是最为美好的。”
他还写道:“可是这与爱因斯坦无关,他的发现在物理学里而不在数学里。”他指出这句赞辞不应被理解为说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而最有意义的这个短语,意思是“具有数学之外的最大的一般兴趣。”被如此赞誉的真理,是哥德尔1930年发现的,那时他年仅24岁。这是他最有名的工作,通常径直称作哥德尔定理,尽管他还发现了许多别的基本定理。这条定理可以按下面随便哪一种形式陈述:
GT 数学是不可穷尽的。
GT1 每个一致的形式数学理论一定包含不可判定的命题。GT2 没有定理证明机器(或程序)能够只证明全部真的数学命题。GT3 没有既一致又完全的形式数学理论。GT4 数学是机械上(或算法上)不可穷尽的(或不可完全的)。
如果我们把“数学”换成“算术”(即数论或关于自然数的理论,是纯数学中最简单和最基本的部分),这些命题仍然为真。简单说来,哥德尔定理揭示了数学(甚至算术)的算法上的不可穷尽性(或不可完全性)。按哥德尔的看法,算法上不可穷尽这个事实,表明了不是人心胜过计算机,就是数学不由人心创造,或二者皆真。因此,这个定理明显地关系到心灵哲学和数学哲学。用哲学的术语来讲,这条定理有助于澄清逻辑与直观,形式与内容,机器与心智,真与可证,实在与可知之间的辩证法。哥德尔定理曾在诗歌(恩岑伯格[Hans Magnus Enzenberger]的“向哥德尔致意”)和音乐(韩策[Hans Werner Henze]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中受到颂扬,也曾在展现图灵(Alan Turing)生平的百老汇戏剧《破解密码》中被引述,又曾在相关的传记《图灵之谜》[2]中被描画。图灵的计算机理论建立在哥德尔定理之上,又加强了哥德尔定理。
哥德尔1931年证明定理的文章,现在有几种英译;这篇文章与哥德尔有关的演讲(1934年,普林斯顿)一道发表在《不可判定的》[3]一书中(此书汇集了与哥德尔定理密切相关的一些基本论文),后来又收入哥德尔的《文集》第一卷[4]。对哥德尔定理的证明,有各式各样的讲解,或书本或文章,数量相当可观,针对的读者群也各不相同。为普通读者写的书里,最可称道的要数纳格尔(Ernest Nagel)和纽曼(J. R. Newman)的《哥德尔的证明》[5];侯世达(Douglas Hofstadter)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6];拉克尔(Rudy Rucker)的《无穷与心智》[7];和彭罗斯(Roger Penrose)的《皇帝的新脑》[8]。
侯世达的畅销书恰在哥德尔去世的后一年问世,哥德尔定理通过这本书给哥德尔带来广泛的声誉,而他本人却与之擦肩而过。这本书写得有声有色,把哥德尔定理与巴赫(J. S. Bach, 1685-1750)的音乐和艾舍尔(M. C. Escher, 1902-1972)的绘画连在一起,认为它们用不同的方式表现了自指或“怪圈”。侯世达把怪圈或“纠缠分层”看成“意识的关键所在”,拟出一首“心智和机器的隐喻赋格曲”。哥德尔证明的构造,支持了人工智能的方案,因为它说明“从高水平看一个系统,包含了低水平根本不具有的解释力量”[9]。
维伯(Judson Webb)也所见略同,他在《机械主义、心智主义与元数学》[10]里论证说,哥德尔定理为许多人工智能学者的信念提供了(正面的而非反面的)证据。另一个极端的观点,以彭罗斯为代表,他说:“从哥德尔定理考虑……我们可以看到,在形成数学判断时,在计算和严格证明起如此重要的作用时,意识的角色是非算法的”[11]。哥德尔自己像思考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人一样,进一步寻找某些洞见,它们和他的定理合起来,即可成功地证明我们自然的信念:人心确实胜过计算机。
希望只要表明心智特别在判定数学问题上的优越能力,就能做到这一点。哥德尔定理在递归论、证明论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里,占据了中心地位。不仅如此,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之也情有所钟。人们问道,在物理学中能不能证明一个类似的定理?[12]也有人建议把定理推广到人间事物里,对此,哥德尔曾经拟出一个他认为合理的表述(在一封信的草稿里──我忘记是给谁的了,日期为1961年3月15日):
1.1 一个完全不自由的社会(即处处按“统一”的法则行事的社会),就其行为而言或者是不一致的,或者是不完全的,即无力解决某些问题,可能是极端重要的问题。在困难的处境里,二者当然都会危及它的生存。这个说法也适用于个体的人。
虽然对哥德尔定理的意义,人们欣赏起来深浅不一,解释起来也不尽相同,但这个定理很快就成为对20世纪思想的一个奠基性贡献。人人都听说过那些奠基性贡献,都承认它们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哥德尔定理就好比弗洛依德的心理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玻尔的互补性原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凯恩斯的经济学,和DNA的双螺旋。哥德尔对逻辑的另外一些重大贡献,虽然在逻辑上很重要而且在哲学上有相当的意义,但没有得到公众如此的关注。他的哲学著作大部分还未发表,发表的只有几篇文章和一些片段。人们耳熟能详的,只是他对他的数学哲学的简略的勾画。
然而,我跟他谈话时意识到这个勾画很不充分,很容易让人误解,就像冰山的一角。仅是我所见的那部分冰山,就显示出一个比平常了解的庞大得多的结构。哥德尔的数学哲学,内容之多让一般人难以置信。
比如说,跟普通的印象相反,哥德尔肯定了我们的数学直觉是可错的,并研究了数学中不同程度的清晰性和确定性。他还承认自然数比任意集合,客观性比客体有认识论上的优先性。他的哲学又比他的数学哲学内容更多。他对许多困难的、看起来远非我们所能知的问题有确定的观点,这一点不同于今日大多数哲学家,一般而言我们对那些问题很难形成这种或那种确信。更有甚者,他的观点通常与时代精神相悖。这种大胆的玄思无疑与他如下的信念相关:“有许多联系,今天的科学和正统的智慧对之一无所知”(1961年9月12日致母亲的信[以下称LM])。
1975年,我应一份通俗杂志之约,写了一篇论文报道我和哥德尔的一些讨论,其中汇集了他对心、物、数学和计算机之间关系的若干观点。哥德尔在审阅论文的某一稿时,要求我加上下面一段话:
1.2 哥德尔告诉我他对心与物有一些深切的信念,他相信这些信念与今日普遍接受的看法大相径庭。采取这些信念的理由乃是出于非常一般的哲学考虑,而且他所持的论证也不能说服信念不同的人们。因此,他只选择陈述部分明确的信念或结论,它们之确定,甚至不须援引他的一般哲学来说明。
在他的深切的信念和他之持有这些信念的理由之间作出区分,暗示了哥德尔对他的一般哲学尚未设想出一个有说服力的表达方式。从我们对他的文字遗产的有限的知识来判断,他的一般哲学的很多内容,似乎并没有完成,也没有付诸笔墨。我的印象是,他没有像在他的数学哲学的某些部分中那样彻底地发展他的一般哲学。甚至有可能,他和我的私下的、不拘一格的谈话,会成为他鲜为人知的一般哲学的各个方面的最丰富、最完整的表达。如果这个猜想是对的话,那么他的哲学观点将容许大量不同的解释。哥德尔思想的发展虽然是个长篇的话题,但这里对其中主要之点略加提示,恐怕是不无裨益的。
1921年,一本微积分基础教程勾起了哥德尔对数学的兴趣。那年夏天,他读了一本歌德的传记,这又间接地引导他对牛顿的思想和一般物理学感起了兴趣。他1922年开始读康德。1924年,他入维也纳大学学习物理;但他对精确性的追求,引他出物理而入数学(1926年),进而达到数理逻辑(1928年)。从他的信中拾出的两则文字,谈了这一段时间里他发人深省的两件事,一是他早早就归附了柏拉图主义,一是他认为自己与当时的知识气氛格格不入。
1.3 大约从1925年起我就是一个概念和数学实在论者(1975年8月19日信,引自RG, p.20)。[13]1.4 我不认为我的工作是“20世纪早期学术气氛的一个侧面”,倒觉得正相反(同上)。[14]
1929到1933年,哥德尔在谓词逻辑和算术基础方面做了根本性的工作,开始考虑集合论了。从大约1933年到1943年初,他主要投身于集合论,又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他关注的中心发生这样的转移,是因为他下决心只把力量集中于基本问题。譬如说,1937年初他告诉我的大学老师王宪钧:
1.5 因为我自己的和其他有关的工作,数论的本质如今基本上清楚了。目前的工作是去理解集合论(“现在么,集合论”)。
1927到1933年间,数学家门格尔(Karl Menger)曾与哥德尔交往频繁。1981年门格尔这样描述哥德尔在科学讨论会上的表现:
1.6 在逻辑和数学问题上,哥德尔慷慨地贡献自己的意见和劝诫。他总是快速和透彻地察觉到问题所在,并用极少的话语做出最精确的回答,经常令询问者耳目一新。他讲这些时好像一切都极为寻常,但又时时带几丝羞涩,油然生出一分魅力,在许多听者的心中唤起温暖和亲切的感觉。
哥德尔从1943到1946年研究莱布尼茨的著作。据门格尔回忆,1932年前后,“哥德尔就已经开始集中注意莱布尼茨了”。他1944年发表了他的罗素篇,1947年发表了他的康托尔篇的第一稿。1946到1950年间,他主要致力于研究时间问题,特别参考了康德哲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他把这称作一次“客串”,结果产生了两篇数学文章和两篇哲学文章。
1951年,他写成吉布斯讲稿,并做了演讲,这篇演讲的主旨是论证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1958年,他发表了贝奈斯篇,把直觉主义数论解释到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有穷数学的一个轻微而自然的扩充里。1953年到1959年初,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写卡尔纳普篇,打算证明数学不是语言的语法,又为某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作辩解。最终他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1959年2月3日,他写信给编者希尔普(P. A. Schilpp):
1.7 我已经数易其稿,但稿稿都不令我满意。提出有份量的、有吸引力的论证来支持我的观点,那倒是容易的,可要完全阐明情势却比我预想的要困难。这个题目跟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密切相连,一些部分还完全等同,那个问题就是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客观实在性问题。鉴于偏见盛行,发表半熟不熟的稿子弊大于利。
哥德尔1959年开始研究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著作。1964年他发表了康托尔篇的修订、扩充稿;1966到1969年他扩充了贝奈斯篇,加了3个新注。1967年12月和1968年3月,他写了两封信给我,解释他的柏拉图主义对他的逻辑工作的重要性。(我后来经他同意,在《从数学到哲学》一书里,发表了这些信[15])。他解释了柏拉图主义与他关于谓词逻辑的工作的关系之后,继续说:
1.8 我可以补充一点,我的一般而言对数学和元数学,特别而言对超穷推理的客观主义思想,对于我其他的逻辑工作也有根本性的意义。
1971和1972年间,哥德尔和我大量讨论哲学,他还对我的一部书稿做了评论。结果他决定通过这本书表述他自己的哲学观的某些方面,把它们公之于众;他的那些简明的陈述刊载于MP:9-13,84-86,189-190,324-326。1975年10月,我们重叙前言,继续讨论到1976年6月。
02
哥德尔的哲学:规划与实行
哥德尔的哲学规划是要发现形而上学的一个严格的理论,大约具有单子论的形式。但是他自忖离此目标道路尚远。他坦言甚至不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初始概念。
他所做的,是仔细处理一些比较容易着手的子问题,表明他的一般态度,和做一些方法论上的建议。现在我的目的是解释他的哲学讨论背后的动机,为此,我把那些讨论看作哥德尔的庞大规划的一部分,但不谈它们与当前哲学的直接联系。哥德尔这样刻画他的哲学:
2.1 我的理论是有一个中心单子[即上帝]的单子论。它在一般结构上类似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2.2 我的理论是唯理主义的,唯心主义的,乐观主义的,也是神学的。
为实现他的方案,哥德尔必须考虑康德对莱布尼茨的批评。他看中了胡塞尔的方法,认为用它可以对付康德的批评意见。由于这个原因,他批驳实证论,维护胡塞尔。哥德尔理论中的乐观主义成分,依我之见应解释为对心灵及其能力的首要地位的肯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拒斥唯物主义。关于单子论的设想,就隐隐然包含了这一点,因为单子被看成精神性的存在,它们组成基本的实体。鉴于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与物分离之心,哥德尔不得不动手反驳这个观点。既然物质力所能及的范围不如计算机的能力范围来得清晰,他假定人脑基本上像计算机一样工作。
然后着手证明心灵比计算机优越,首要的证明步骤是论证心灵比计算机能处理更多的数学。换言之,为了论证他的唯心主义,哥德尔尝试把形式与直觉的辩证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使问题更接近于获得精确的解答。这与他在数学基础领域的工作是一脉相承的,他的逻辑上的精确结果,对一种实证论味道十足的形式主义来说,构成了正当的和精致的反驳。再举一个决定性不那么强的例子:他相信我们对时间的直观概念不是客观的,他对爱因斯坦的场方程的解既受这个信念的促动,又被他用来支持这个信念。
哥德尔理论中的理性主义成分既维护了柏拉图主义,又维护了心灵的优越地位,因为理性主义,至少像哥德尔理解的理性主义,以共相为中心,把共相视为稳定的和可知的。与他庞大的规划直接相关的,是形而上学或单子论的初始概念的独立存在和可知性,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制约整个理论的公理,并把它们看作真的。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哪些是初始概念。无论如何,从哲学史的经验来看,要拣选形而上学的初始概念,那些熟悉的候选者恐怕都不够鲜明,可知性不够充分,不足以让我们达成主体间稳定的一致,看出它们的公理是真的。哥德尔的典型作法是,不直接面对这个问题,而集中力量处理一个比较确定的相关子问题,即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或客观主义)问题。
然后他似乎使用了他的不受限制的概括(和类比)原则,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思考足够努力,并且正确看待事物,那么形而上学概念就会变得与数学概念同样鲜明,同样清晰。他的理论中的乐观主义的和神学的成分,是用来增强我们的力量的。不受限制的概括原则是乐观主义的一个主要应用。这两个成分其他的具体应用,在哥德尔关于来世和上帝存在的论证中,有充分的体现。他显然意识到,对于不相信那些结论的人,这两个成分不能让他们信服。实在讲来,它们在哲学中只有助探的价值:相信它们的人可以借助它们达到某些结论,然后再寻找或者说找到更广泛为人接受的论证,来支持那些结论。他思考作为概念理论的集合论和逻辑。
就此而言,他反复探讨了对逻辑的一种构想。弗雷格(Gottlob Frege)曾有把逻辑当作概念理论的不一致的构想,在我看来,哥德尔的构想对是弗雷格的构想的一种自然的润色加工。二者都把集合论当作逻辑的一部分,区别在于弗雷格假设每个概念的适域都是一个集合,而哥德尔则放弃了这一假设。结果,虽然集合论大大丰富了逻辑,但概念理论并不与它平行,而且还有待发展。概念理论的主要公理是什么,眼下我们还一无所知。哥德尔除了考虑集合论的内在意义,还对探察数学的本质有兴趣,一来这可进一步支持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再者这也是他心目中的逻辑的一个实质性部分,在他看来,逻辑是单子论的一个补充成分:
2.3 逻辑处理更一般的概念;单子论包含生物学的一般规律,它比较具体。
在上一节里,我尝试把这里所考虑的哥德尔的观点看成他宏大的规划的组成部分。这个规划的宏大目标乃是发展一种精确的理论,对形而上学做一番恰如牛顿对物理学所做的事业。我肯定今日我们大多数人看不到一条可行的道路,能达成这个目的,同时能够曲尽其妙,不有所缺失。虽然如此,但总有可能沿着目标的方向预见一些成果,足以勾勒出一种单子论的大体轮廓。譬如说,我们可以对维特根施坦(Ludwig Wittgenstein)《逻辑哲学论》里的世界理论做些扩充,在概念和客体(单子和所有客体集)之间做出区别,把知觉和欲求作为单子的原始官能,将莱布尼茨的一些原则和约束知觉与欲求的一些基本规律当作公理,如此我们就可以希望得到与我们粗糙的直觉相符的一个合理的理论,特别地,还可以看到哥德尔意义下的真逻辑命题按照这个理论在所有的可能世界里都真。
考虑到后面第9章里讨论的相关的思想,我觉得有可能在这种明显弱化了的意义下解释哥德尔的规划。根据目前的哲学状况和我自己的哲学研究,我相信可以把我所知的哥德尔哲学观点分成两部分,把二者分开来评说。一方面,对上帝与来生的玄思和单子论里的中心单子超出了我的所思所虑;他的哲学里的乐观主义和神学的部分,我看不出足够的合理性,无法从中得益。另一方面,哥德尔的方法论视角和他对诸多知名哲学家的评论,却极富启发性,能帮人开阔眼界;他大量讨论了逻辑和集合论,心与机器,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等问题,这些讨论是对欧洲哲学传统延续至今的对话的充满活力的贡献。
的确如此,甚至可以说哥德尔在其哲学的第二部分(方法论)里,正是关注着这个传统的基本问题。这个传统以知识哲学为中心,注重普遍的和理论性的东西。它思索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堪称希腊哲学的中心问题),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堪称近代哲学从笛卡尔、康德以降的中心问题)。譬如,柏拉图的相论乃是要解决共相的问题,又被公认为他的哲学的基石。但这只是一位哲学家的知识哲学,不是整个工作的一般性的定义。车尼斯(Harold F. Cherniss)谈论柏拉图学园的时候,这样描述了哲学的任务:
2.4 有两样东西,柏拉图对它们的兴趣比对相论本身还要浓,因为相论归根到底不过是他用来满足这两项要求的工具:第一,有一个叫心的东西,能够了解实在;第二,作为知识的对象的实在有绝对的、无条件的存在。
这两项要求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满足。实际上,我们都相信它们确确实实被满足了,这是我们从经验里知道的。但是我们要来反思一下的时候,却发现很难确定实在是什么,或实在意谓什么,也很难确定在什么意义上和在多大程度上我们的心能够了解实在。传统哲学的很大一部分便是要来把握这个无条件的、绝对的实在概念,刻划人心了解它的能力范围。关于心对实在的了解,它的成功与失败,我们的经验可谓不胜枚举。我们确信物理世界是实在的,我们所知的生活,包括科学技术令人惊异的成功,也说明人心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了解物理世界。然而,即使只涉及最初等的知识,我们的心也必须使用概念,像红、椅子等等,它们不像具体的红椅子那样存在于物理世界中。我们于是面对着概念究为何物的问题。
因此,哥德尔50年中执着地追求、不断地探索令人信服的理由来支持某种形式的柏拉图主义,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按车尼斯(2.4)的提法,我们可以说知识哲学的主要问题是(1)客观实在的范围与本性;(2)人心了解客观实在的能力的范围与本性。大多数人同意物理世界是客观实在的一部分。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有名的(1a)共相问题,它一起头便问道:概念或共相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客观实在的,在什么意义上是客观实在的?(这问题的另一部分是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另外一个基本问题是(1b)时间问题,它问道:时间和变化是不是客观实在的?
我们从经验中知道,心对物理世界有许多知识,这一点不论从我们日常的知识还是从我们今天掌握的物理学中看,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还知道,心对数学世界也有许多知识,因为我们有丰富而可靠的数学。大多数人同意感官经验在我们的知识中起重要作用,但这绝不是说仅仅用感官经验就能解释概念性知识,而概念性知识不但在物理学中起重要的作用,它在数学中的作用,甚至更加突出。自然就会问到,(2a)心既然能够具有概念性知识,尤其是能够了解和应用数学,那么这种能力的范围多大,本性如何?因为我们感觉对物理世界已有相当的了解,又因为我们把人脑当作它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就想弄明白(2b)心和脑的关系,特别要比较它们的能力。既然计算机的运作方式比心和脑更加显明,那么另一个熟悉的问题就是,(2c)心或脑的功能是否像计算机一样,还是它们能比计算机多做一些事情?我粗略勾画的这5个问题,以扑朔迷离和聚讼纷纭著称。讨论它们的时候,我们典型的话不投机,因此就难以发现激烈争辩背后的真正的分歧何在。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策略,可用来对付这个困难,一个是把一种立场的所有分支详尽摆出,以期更加确定地揭示它的特点;另一个是把复杂问题分成简单的部分,想办法从那些能够精确处理的部分入手。
据我看,哥德尔的大部分工作是以第二种策略研究哲学。哥德尔的哲学观点和数学发现大都能归入上述5个问题的范围里,针对这些问题的一些加了限制的,或者引申出来的分支。他把1a,即共相问题,主要限制到数学概念及其关系上,力图确立它们的客观实在性。的确,在他的哲学著述和谈话中,这个问题讲的比哪个问题都多。至于1b,他与康德(还有巴门尼德和“近代唯心论者”)所见略同,认为时间和变化仅仅是主观的(不是客观实在的)。
具体来说,他用他对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解──这是个严格的数学结果──来支持这个信念。关于2a,心对概念性知识的把握,哥德尔也是首先集中考察数学和逻辑概念。他论证道,我们的直觉超越了康德式的(或者按他的说法,具体的)直觉,我们确实可以感知概念。康德的Anschauung局限于时空(或感性)直觉;它多少解释了希尔伯特的有穷数学,这种数学带我们越过有穷,到达一种简单形式的潜无穷。希尔伯特自己曾希望用他的有穷数学借助一致性证明来维护更高等的数学,但哥德尔定理却使这个希望受到挫折。哥德尔隐约提出一种方法,它与希尔伯特原先的规划相伯仲,目的是提示我们如何通过增加适当的新抽象概念来一步步扩张希尔伯特的有穷数学,藉此得到越来越高等的数学。
哥德尔对问题2b和2c也颇有兴趣,就是说,他研究心、脑和计算机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比较它们的能力。他相信,“人脑基本上像一台数字计算机一样工作。”利用这个假定,他提出了一个“科学上可以证明”的猜想:心比脑(视为计算机)能做更多的工作。他还进一步提出几种建议,沿着这些建议的方向我们有希望证明心比任何计算机都能处理更多的数学。特别地,他寻求一些适当的前提,单个拿出或合盘托出,再加上他的数学不可机械穷尽的定理,就可以推导所要的结论:在数学上,心比计算机更加优越。就心把握实在的能力而言,概念可谓极端重要。当我们想着一个新概念的时候,我们是在发现,在创造,还是在发明那个概念?围绕这个问题有无穷无尽的争论,答案取决于人们对1a,即共相问题采取什么立场。
然而,不管这些立场如何,人心习得或思索新概念的能力总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和难以把握的属性。哥德尔和我们许多人都感到,这种恒常的发展远远超出计算机的能力。不过很难看出怎样令人信服地证明情形就是如此。对我来说,人心习得或思索新概念的现象是一个核心的奥秘,哲学试图清晰透彻地解释它,但是屡试屡挫。我倾向于认为,许多哲学争执,不过是这个事实的后果,问题1a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哥德尔运用他的不受约束的概括原则,不但得出理性能够回答自身提出的问题这样强的结论,而且借助类比扩大了某些概念的适用范围。因此,他的一些术语就可能误导读者,甚至可能掩盖了一些困难。
譬如,用我们对物理客体的感知作比,他声言我们也有能力感知概念。然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他这话的意思首先是说我们有能力去进行理解,有能力看出关于那些概念的某些陈述是真的。他也把感知概念或直观本质当作一种观察。公理方法在他看来不是别的,就是清晰的思维。他对公理方法的看法比一般的看法来得宽泛,颇令人揣摩。稍后我会试着揣测他的看法,作一些解释。对概念,一般熟悉的看法是,它原本是心所设想出来的某种东西。哥德尔反其道而行之,把概念当作实体──具体来讲,“当作独立于我们的定义和构造而存在的事物的性质和关系”。
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区别这样的概念和那些我们为辨别与理解的目的而引入的概称[16]:我们显然在使用这样的概称,不管我们是否也在其中看出了哥德尔意义下的真实概念。他自己在刚才引用的那句话的上下文中提到了一类这样的概称。哥德尔区别了创造,即从无中造出某物,和构造或发明,即从他物中造出某物。他严格遵从这一区分,致使他的创造一词,使用起来比我们熟知的要狭窄。特别是他把概念和其他我们构造的东西看作发现,而不是创造。结果他就与布劳威尔(L. E. J. Brouwer)持不同论调,说是我们从原初的二一性(two-oneness)中构造出──而不是创造出──自然数来。
我通常按宽泛的、相对而言较稳定的意义理解直觉和理想化,我相信这与哥德尔基本设想并无二致。我也把全部的初始概念看成是通过理想化而得到或发现(在他的意义上)的。我认为直觉的领域首先包含罗尔斯(J. Rawls)所称的“反思均衡中审慎的判断”。
03
哲学与数学和逻辑的关系
欧洲哲学中逻辑和数学突出的核心地位,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这无疑是因为这些学科异常精确,同时又涉及最高的普遍性。一般大家都同意,数学在柏拉图哲学中扮演重要角色,亚里士多德是逻辑的建立者。笛卡尔和莱布尼茨的著作在哲学和数学中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斯宾诺莎按几何推理的次序来安排他的《伦理学》。虽然康德把形式逻辑贬到边缘的位置,他的先验逻辑却稳居他的哲学的中心。黑格尔的逻辑学则是他的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
到了20世纪,数学和逻辑对哲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弗雷格(1848-1925)、胡塞尔(1859-1938)、罗素(1872-1970)和维特根施坦(1889-1951)都从数学基础起家。我们都熟悉他们的著作的重要性和他们对现今和当代哲学的影响。进一步讲,戴德金(Richard Dedekind, 1831-1916)、康托尔(George Cantor, 1845-1918)、庞加莱(Henri Poincaré, 1854-1912)、希尔伯特(1862-1943)、布劳威尔(1881-1965)和图灵(1912-1954)虽然主要以数学家闻名,但对数学哲学有深广的影响。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 1839-1914)、怀特海(Alfred N. Whitehead, 1861-1947)、C. I. 路易斯(C. I. Lewis, 1883-1964)、贝奈斯(Paul Bernays, 1888-1977)、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拉姆赛(Frank Ramsey, 1902-1930)、哥德尔(1906-1978)和蒯因(1908-1999)都同时研究逻辑和哲学;他们的著作显示了把逻辑和哲学相联的几种不同的途径。有效的思维,其特色即是把形式的和直觉的适当地融合起来。数学和逻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形式与直觉相互作用的一个模型和一个参考系。
在日常生活中和科学思维里,我们总是在使用逻辑和数学,有时含而不露,有时则大张旗鼓。在哲学中,我们进而探讨它们的本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与哲学的关系。哲学在数学中发现了清晰思维的典范。明晰透彻的概念,确定无疑的结论,还有秩序井然的论域──纯粹理性的力量在这里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柏拉图和哥德尔都把我们的数学经验当作主要的证据,来支持明白的概念的独立存在。前面已经说过,斯宾诺莎用几何学的方式把他的哲学系统组织和表述成一个公理理论。弗雷格努力寻求数学的严格的基础,结果获得了一般的哲学框架,用来研究所有科学话语中的意义和真等概念。
哥德尔把对立的哲学当作不同的世界观,将数学视为他所钟爱的那种哲学的最后堡垒,那种哲学把世界看成一个有秩序有目的的整体。哲学对数学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显著、那么深入了。康托尔确曾尝试从神学汲取力量,支撑他的集合论,罗素找不到宗教信仰的理性基础,则转向数学寻求安身立命的根本。哈代(G. H. Hardy)和别的一些数学家似乎觉得柏拉图主义哲学对他们的数学工作在一般的方面有所帮助。哥德尔独竖一帜,宣称──并且特地解释了为何──他的数学哲学里的柏拉图主义立场对于他的逻辑研究里的数学工作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哲学对逻辑的关系比它对数学的关系更加直接和密切。逻辑被当作哲学的分支来教,在一些哲学里,逻辑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据了中心地位。然而我们知道,不仅对逻辑的本性人们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对逻辑的范围也是歧见纷呈。我们都在思维里默不做声地使用逻辑,但是只有不多的人把逻辑本身作为一门学科有意识地加以研究。
逻辑作为一种活动,即思维的艺术,裁决信念与行为间的相互作用,或如人们所认为的,裁决二者之间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又在我们的思维过程里包含了主体与客体间的、已知与未知间的、主观与客观间的、形式与内容间的、共相与殊相间的、和形式与直觉间的辩证法,而且前者在思维过程中常常被后面诸项取而代之。逻辑的裁决作用表现在各式各样的思维当中。作为一种艺术或方法,逻辑对我们思想的材料来说,是中立的。辩证法一词虽然模糊,但颇有意味,普通用它来描述对立的或相反的力量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在某些过程里导致一个更高的更统一的阶段。
传统上,辩证法与逻辑紧密相连。在整个中世纪里,辩证法一词都指称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逻辑。对黑格尔来说,逻辑是辩证过程的科学,而辩证过程是对立面在部分与整体的复杂关系中持续不断的统一,它渗透在人类思维中,也弥漫于世界历史里。人们熟知的对逻辑的题材的刻画,起头便是赞同逻辑真理包含而且只包含有效的命题,有效的意思是说,不管那些概念和客体在现实世界里是怎样的,这些命题都真。逻辑概念或逻辑常项因此便是有效的命题中出现的那些基本的或不可替代的概念。举例来说:每样东西等同于自身;每个命题蕴涵自身;或者一命题为真,或者它的否定为真,但并非二者都真;某事对每样东西成立,如果它对所有的东西成立。这些是有效的命题,因为不管那些概念和客体为何,它们都真。等同、蕴涵、否定、全称(所有的)等等,是出现在这些命题里的基本概念,它们便是逻辑常项。
进一步说,所有的命题都是由简单的谓述命题──即那些把某些概念应用于某些事物的命题──经过这些熟知的逻辑常项组织而成的。为了用统一的方法有效地处理命题,逻辑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弗雷格发明了越来越充分的结构和记号,用来整饬建立命题的直观过程。今天普遍接受的谓词逻辑系统,就其一般形式而言,正是弗雷格1879年建造的系统。在实践中,没有人否认谓词逻辑的确是逻辑的一部分。一场人们熟知的争论,集中在谓词逻辑是不是整个逻辑这个问题上。有可能重新构建谓词逻辑,使它看上去与管理它的逻辑常项(等词、命题联结词和量词)的推理规则打交道。
譬如,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完备的谓词逻辑系统,只采取事物的自我等同和命题的自我蕴涵作公理,把系统的主干让给刻画了逻辑常项的直观意义的自然推理规则,例如允许从两个给定的命题推出它们的合取的规则。用这个重构的谓词逻辑,那些希望把逻辑限制到谓词逻辑上的人,就可以诉诸人们熟悉的逻辑观念,将逻辑当作研究有效推理的规则的科学,以此来支持他们的论题。要决定客体的范围,我们可以从熟知的物理客体出发。当我们考虑概念时,我们就被引向客体王国的一个自然的扩张:盘算我们最熟悉的概念,每一个都有一个对应的集合作这个概念的外延,就是这个概念能够应用于其上的所有事物的聚合。然而,正如弗雷格已经强调的,把外延设想成客体是很自然的。于是我们就被导向这样的观点:客体的集合也是客体。既然逻辑研究必然的东西,就是说逻辑真的命题在一切可能的经验世界中都真,它就不会言及偶然的事实,像这个或那个经验客体或概念在现实世界里存在等等。
这样一来,好像营建逻辑就没有了质料。然而,即使不承认任何经验的事物,我们仍然认识到一定有某个空概念,它不能应用于任何事物,因此就有一个空集,它是每个空概念的外延。所以,在每个可能世界里,都至少有一个客体,即空集。但给定任何一些客体,我们都能建构它们的集合,它们的集合的集合,等等。用这个方法,我们就得到人们熟知的纯集合的分层,这是集合论研究的题目。因此我们可以说,集合论也是逻辑的一部分。同样有可能预见一个类似的纯概念的理论,并且根据相同的理由论证它也是逻辑的一部分。
不过我们知道,有些概念的适用范围并不构成集合:例如,概念的概念或集合的概念。由此可见,纯粹概念论并不全然是纯粹集合论的翻版。实际上,虽然眼下我们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发育良好的集合论,但要得到一个同样成熟的概念论,还有漫长的路程。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基础工作留待人们去做,甚至在建立逻辑的基本框架方面,也仍然任重道远──只要把概念论看成逻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情形就是如此。我先前已经说明,对逻辑的这种看法,我相信既应和了弗雷格的设想,又阐释了哥德尔的宣言。
哲学和逻辑的关系从这方面看来,与科学和数学的关系颇有相似之处。数学研究所有科学共同关心的一般的和抽象的方面,类似地,逻辑的课题可以看成从具象走向抽象时我们所有的哲学关切的共有成分或者说极限。我们也可以把逻辑看成一种形式的本体论,它构成了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的部分。关于逻辑和哲学的关系,说得不那么抽象一点则可采取如下的观点:哲学作为世界观其目的乃是捕捉和描画我们的内部资源的一般的和综合的框架,借助于内部资源,我们接受、消化和解释我们关于世界和关于我们自身的所有的思想。照这样的看法,逻辑组成了哲学的一个主要部分,甚至可以等同于所谓的纯哲学。依我看,黑格尔的逻辑观和维特根施坦在他的《论确定性》一书中发展的观点,倾向于对逻辑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作这种解释。
我们每个人都学着去相信一些东西,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信念系统,作为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学着按照那些信念行事,有些信念坚实稳固,就像河床,还有些多少变动不居,就像流水。逻辑研究所有的信念系统中那些坚实稳固的信念。某些经验命题中的信念,即便不是逻辑的一部分,但也属于我们的参考框架。数学是逻辑的一部分。虽然同一个命题既可以看成一种检验规则,又可以在别的时候看成必须用经验来检验的东西,但逻辑不是一门经验科学。以上是在维特根施坦文本的基础上,加上一种解释和说明,对逻辑作的一番粗略的刻画。但是这种刻画依然歧义杂陈,包含进一步精释的多种可能性。
譬如,黑格尔和维特根施坦虽然都可以说运用了这种逻辑观念,但给出的答案却不同──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同一和差别有不同的态度,也由于他们对什么是知识有不同的想法。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按照这种观念,逻辑形成了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我们要求这种逻辑观念再精确一些,我认为未尝不可以把弗雷格—哥德尔的构想,当作它的一种精释。要把这种逻辑观念──即把逻辑看成不同的信念系统的共同部分──和我们熟悉的共同关切联系起来,一个办法是与罗尔斯的工作相比较,罗尔斯用正义的政治观念来替换综合的政治理论,而正义观念的用意是代表现代民主社会里相交的合意。如果考虑相互冲突的哲学世界观的共同部分或整个相交的合意,我们就似乎有了一个比较踏实的方法,来逐步确定先天的东西的模糊领域,所谓先天的东西是指我们潜在地能够独立于我们特别的个体经验而得到和接受的那些概念和信念。
换言之,我们可以不把自己限于一种类型的社会,尝试寻找所有不同的世界观共有的概念和关于它们的信念。如果把逻辑的范围等同于先天的东西的范围,或者可能它的极大普遍的部分,我们就在逻辑里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藉之我们可以希望在相互冲突的综合哲学之间做出裁决。数理逻辑按今天一般的理解来说,大体包含递归论或计算理论、证明论和构造性数学、模型论、和集合论。它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如果我们把逻辑限于这种意义上的数理逻辑,那么哲学和逻辑之间的关系就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一般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形。整体说来,数理逻辑的发展,特别是在它早期的阶段,深受哲学关切的影响:……[17]反之,它对数学哲学作用之巨,可谓入木三分,影响由此及于一般哲学的几个基本部分。人们对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见仁见智,态度不一。比如爱因斯坦曾说:“认识论和科学的相互关系值得玩味。它们互相依赖。认识论若没有科学相伴就变成空架子,而科学若没有认识论,无论怎么想象,都是粗陋和糟糕的”。但今天大多数做实际工作的物理学家对认识论不屑一顾。
同样,今天大多数做实际工作的数理逻辑学家不像哥德尔,他们对哲学至多有一点浅表的兴趣。态度上如此大的差异,无疑与个别学科当前的发展状况有关,也与科学家个人研究的具体问题有关。无独有偶,不同的哲学家对哲学和科学的积极关系或珍重有加,或啧有烦言,这取决于他们对两科抱怎样的看法,和他们对哲学中何者为要的偏好。哥德尔认为科学与哲学的相互作用有利于双方。
另一方面,维特根施坦却觉得科学有害,因为它增强了“我们对概括的渴望”,而这种渴望导致坏的哲学。他认为真的哲学与数学无干──虽然他有时声称哲学可以帮助科学转到迎合我们的真正需要的正确轨道上来。
实际上,我们的确从科学结果中抽出哲学结论来,不管是有所收益,还是徒增迷惑。我们都知道,科学和宗教有冲突,科学的发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整个的看法。职业哲学受重要的科学进步的影响,如牛顿物理学、达尔文生物学、相对论、量子物理学、和分子遗传学。其他人且不说,哥德尔自己曾反复考虑他的不完全性定理的哲学意蕴。
另一方面,说到哲学对科学的影响,我们知道许多科学思想从哲学中萌芽。神学中颁布自然律的上帝,对牛顿那样的物理学家孜孜不倦地追求自然秩序,很可能有积极的影响,本世纪中,爱因斯坦和哥德尔都提到哲学对他们的科学工作的有力的促动。哲学和科学相互影响的一个显著的例证,是希尔伯特方案里提出的一系列富有成果的数学问题,它们是借助想象和技巧从关于数学基础的哲学争辩中提炼出来的。
在这类情形里,科学问题的解答也有助于澄清原来的哲学问题。哥德尔看到哲学的一个作用是提供初生的思想──比如原子论,这是德谟克里特提出的,另一个作用是把哲学问题还原为科学问题,他提议寻找心优越于物的科学证明来澄清关于心与物的哲学问题,其用心即在于此。
再者,哥德尔相信能找到精确的形而上学,这个信念似乎出自他对我们数学和物理学经验的反思的大胆的──虽然不那么令人信服的──外推。哥德尔世界观的各个部分具有不同程度的清晰性和确定性;它们结合在一起,乃是由于一种对于不同程度的说服力的多少不受约束的概括。他的数学方面的工作是确定无疑的。他把逻辑作为概念论的设想,界定了一项相当精确和引人入胜的任务,虽然我们眼下还不知道,致力于发展这样的一个系统所得究竟如何。哥德尔的数学中的柏拉图主义意味深长,它包容了一套解释的谱系,从较弱的过渡倒较强的,从浅白易解的直达深沉宏博的。他含蓄地拿数学类比形而上学,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这同时提示了一些与他的意图相符的可能性,虽然不够切实,但也不乏可行性。
毫无疑问,不同的人会接受哥德尔世界观的不同部分,从中汲取不同的教益。我相信,关于他的工作的几个部分的不同程度的确定性和说服力,大部分哲学家多少会同意我的分类和评价。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的一些想法不无道理而且颇具吸引力,因此希望进一步澄清和发展这些想法。另一些人则可能把他的大部分哲学思想视为无稽之谈,将他的坏哲学和他的逻辑上的好工作区别对待。
注释
[1] 参见王浩Reflections on Kurt Gödel(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87)(以下简称为RG)第31-32页。中译本名为《哥德尔》,康宏逵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出版,相关页数为第47页。──译者
[2] Andrew Hodges, Alan Turing: the Enigma. Simon & Schuster, 1983.
[3] Martin Davis (ed.), The Undecidable. Hewlett, New York: Raven Press Books, Ltd., 1965.
[4] Kurt Gödel, Collected Works, vol. 1, ed. Solomon Feferman et. 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5] Nagel, Ernest, and J. R Newman, Godel's Proof.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8.
[6] Douglas R. Hofstadter, Gödel, Escher, Bach: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Basic Books, 1979. (此处用郭维德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标题。──译者)
[7] Rudy Rucker, Infinity and the Mind. Birkhauser Verlag, 1982.
[8] Roger Penrose, The Emperor’s New Mind. Oxford University, 1990. (中译本见:罗杰·彭罗斯,《皇帝新脑》,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译者)
[9] Hofstadter, 1979, p.707.
[10] Judson Webb, Mechanism, Mentalism, and Metamathematics: An Essay on Finitism. Reidel, 1980.
[11] Penrose, 1990, p.416.
[12] 比较RG, p.156.
[13] 参见RG的中译本第31页。──译者
[14] 同上。──译者
[15] Hao Wang, From Mathematics to Philosophy (以下称MP).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74, 8-11.
[16] 康宏逵用“概称”翻译notion一字,此处沿用这个译法。参见《哥德尔》(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页436注2,页444-5。──译者
[17] 原文如此。因本书未经作者最后校读,疑此处作者原想加入部分内容而最终遗漏。──译者
本文原文刊于《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6期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