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稿 | Fernando Chirigati(《自然-计算科学》主编)
翻译 | 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
Saul Perlmutter博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NL)的高级科学家,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此,他向我们介绍了宇宙的加速膨胀,以及计算机技术在该领域的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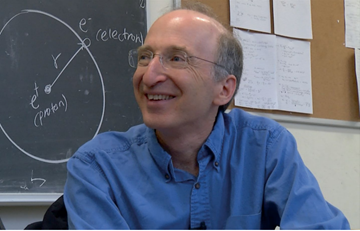
2011年,Perlmutter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扬他和其他科学家透过观测遥远超新星而发现宇宙加速膨胀。Credit: Jon Shainker
您能解释一下宇宙膨胀的含义吗?
许多人听到宇宙膨胀的第一反应是,宇宙怎么能膨胀?毕竟,人们可能认为宇宙即一切,因此它没有膨胀的余地。但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无限的宇宙。我们置身于星系的海洋里,这片星海在任一方向上都延伸到无穷远处。所以,不管我们是用大型望远镜向上看,或是透过地板向下看,还是从侧面看,都会看到一个又一个星系。在这片浩瀚无垠的星海中,星系之间有一个平均距离。也就是说,沿着给定的方向从一个星系驶向另一个星系,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宇宙在膨胀的意思是,星系间的距离在随时间慢慢增加,星际旅行所需的平均时间也在逐渐变长。如果你要问,究竟是什么在膨胀?膨胀的部分到了哪里?那么很遗憾,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只是宇宙中任意两点间、任意两个星系间的距离在增加,就好像我们把它们从中间吹开了一样。这可能有些费脑,但宇宙的确是这么发展的。这也意味着,如果时间倒流,星系和点之间的空间就会变少,它们之间的距离会拉近。换句话说,宇宙会变得更加致密,但仍然是无限的!倘若回溯得足够远,在某一时刻我们会发现所有物质都重叠到一起。此时的宇宙虽然仍是无限的,但就像一锅致密的热汤——我们一般将该阶段称为“宇宙大爆炸”。那我们不禁要思考,在此之前的宇宙是怎样的呢?目前这仍是未解之谜。
图源:Pixabay
为什么超新星特别适合用来观测宇宙膨胀?
要想测量不断膨胀的宇宙中两点间的实际距离,我们需要相应的测量标尺。自上世纪30年代首次观察到恒星爆发/超新星起,人们就在思考超新星能否用于测距,但一直没有定论。到了80年代中期,人们发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爆发恒星(Ia型超新星)。这类超新星的光谱稳定不变,因此极易辨认,可作测量器使用。这类超新星像烟花一样先变亮后变暗,但亮度峰值近乎恒定。因此,若能测得超新星爆发的亮度峰值,便能将其作为标准烛光来测算超新星与地球间的距离。如果我们观察到超新星的光亮越来越淡,这表明它正离我们越来越远。通过分析其亮度,我们能准确地获得距离变化量。但要注意,这一规律仅适用于Ia型超新星。
宇宙为什么会膨胀?
目前有很多解释宇宙膨胀的理论概念,它们本质上都源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是为了探讨万有引力的原理,以及近光速运动物体的参考系问题。但在此过程中,他意识到相对论也能用于研究宇宙。当他和同行们通过计算描述宇宙时,他们认识到宇宙并非静止,而是趋向于膨胀或是收缩。按照广义相对论,宇宙不可能静止不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宇宙的状态是由万有引力、空间和时间的运作方式决定的。有些物质会促使宇宙膨胀,有些物质会促进收缩。例如,在更为致密的宇宙中,大量物质因万有引力而相互吸引,那么宇宙膨胀的速度就会趋于减缓,甚至发生收缩。
计算科学如何助力您的研究?
天体物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常常会关注宇宙中出现的奇异事物。如果我们对这些事物研究得足够久,那我们的确能取得一些新认识。而我的关注点与其他人稍有不同。我想问的是,万有引力是否会导致宇宙膨胀减缓,最终停滞并坍塌呢?研究这一问题还能回答我的另一个疑惑:是否有可能,宇宙空间并非无限,而是在广义相对论的框架下,自身向内弯曲呢?但要想解答这类问题,首先需要回顾宇宙的膨胀史。理论上讲,单独研究任何一颗超新星都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我们关注的是膨胀过程中的时间变化:如膨胀速率是否有所变化?是否会变慢?因此,我们需要研究完整序列的超新星——几百万年前、十亿年前、五十亿年前、七十亿年前,一百亿年前以及更早的超新星,以判断膨胀过程是否有变化。我们需要观测大量的超新星,而且要从不同方向上对比,以免某个方向的超新星过于特殊。由此可见,我们的研究问题带有几分统计性。此外,寻找超新星也是一个统计问题。单个星系在一千年内通常只会发生几次Ia型超新星事件。我们没有这样的耐心,而且我们的研究生也等不了那么久!因此我们希望观察上千个星系,这样才有机会在实验期间捕捉到足够的(数十个)Ia型超新星。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开发一种能同时观察上千个星系的技术。这一定程度上是仪器问题——我们要研制一款超广视域望远镜相机,才能同时观察多个星系。但很快我们发现,这也是一个计算科学问题。因为我们得设法从拍到的不同星系的广域图像中寻找这些微小的亮点,并从这些亮点中找到更小的、代表着超新星的亮点。这份任务交给计算机来做,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项研究的实现借助了哪些技术?
从技术上看,可以说我的研究正当其时。首先,借助上世纪80年代初问世的电荷耦合器件(CCD)相机,我们能有效地将望远镜中的图像数字化。其次,当时的计算机在使用上已大大简化,运算速度也十分可观。我们利用计算机实现了望远镜的自动化——高效的夜间连续拍照,并快速处理海量的图像数据。虚拟内存在当时也开始兴起,它省去了程序开发中内存交换编程的麻烦,使大型图像的处理更加简便。此外,新兴的计算机网络也帮了大忙。不然我们还得把调制解调器带到加那利群岛、澳大利亚和智利等地,用电话线传输回数据!除了上述技术,我们当时还用到了LBNL的大型计算资源。总而言之,彼时我们正处于技术前沿,能够开发出考虑不同类型的噪音,并进行图像对比的新软件。随后,我们开始研发超新星精确找寻技术,这项技术改变了整个研究领域。在此之前人们都是随机地寻找超新星,但有了这些技术,我们能提前制定计划,发现一批超新星。当时,没人预测过超新星的发现,而且每次最多发现一颗。计算技术在这项研究中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那时都在学习数据分析、数据压缩(我们是最早一批小波压缩软件开发者!)、数据储存、用户界面设计等技巧。
在您的研究领域中,今后有哪些必须要解决的计算问题?
如今,计算机性能带来的最明显的影响是,我们在许多情况下都直接把模拟作为一种全新的统计方法。我们利用正演模型并重现所有的系统条件,以获得置信区间。这将会推动计算机朝着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因为我们常常要模拟成千上万的数据版本,并进行成千上万次分析。因此,我们必然需要更强的计算能力。(但个人而言,我们尚且无法构建严密且有效的计算管线来追踪数据和软件的更新,了解不同的分析变体之间的对比方式,并据此理解数据中存留的系统不确定度。)最终,这也将帮助合作者们判断他们推进到了哪个阶段,了解当前认知建立的基础,并分析与目标之间的差距,共同实现软件的高效构建。此外,我认为研究人员得更加重视盲态分析:在调试管线直至你满意的过程中,你不会关注答案。除非我们嵌入所有的盲态分析技术,否则很难改变这一现状。计算机相比人类能更有效地追踪事物。但如今很多情况下我们还在依靠人力,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机器学习应用于天文学和宇宙学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每当有新的计算技术问世,我们都会想要试试这些技术能否用在宇宙学和天体物理学中。比如,当人们开始研究分布式计算的时候,我们也会学习如何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分布计算。机器学习也是如此,如今该技术正极大地影响着天体物理领域。以Ia型超新星为例,过去我们一直将其视为一类事物,而如今我们认为它们是恒星爆发的类似组,或由一到两个相似的前身恒星所引发,每颗超新星都由其精细爆发图像所表示。我们利用机器学习来分辨相似的超新星,识别不同的超新星,并据此进行组间对比。我们还利用机器学习来消除天空图像分析中的假象。人眼能轻易发现分析中的错误,但如果要交给计算机来做,那么机器学习便成了一个情理之中的选择。研究人员在宇宙模拟中也会用到机器学习:如果我们大概知道从一个阶段演化到下一个阶段会发生什么,我们就能用机器学习来模拟这一过程,从而跳过费时的多体问题。
如何看待您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和实际观察之间的协同?
物理学是一个综合领域,宇宙学是其中的一个分支领域。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物理学和宇宙学都经历了十分有趣的发展,并逐渐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偏重理论,另一部分偏重实验和观察。一般来讲,我们会先进行观察,并思考现象背后的过程。随后,理论学家会就这些观察结果提出充分约束的预测性理论。倘若该理论的确十分可靠,那么我们便能据此对实验或观察的对象进行一定的预测。最后,这又进一步促使观察者和实验者设计实验以检验预测结果。然而,这一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例如,在我的研究领域中,现有的预测性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宇宙加速膨胀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与理论学家反复探讨,并不断改进我们的观察。如果运气够好,我们会发现一些奇特现象,而这些现象会迫使理论学家们反思并完善其理论。在我们这个领域,很少有学者能两者兼顾。因此,实验者和理论学家要多加合作。但相较于理论学家,我们实验者的工作往往更加耗时。因为搭建仪器并采集数据可能需要好几年,乃至数十年之久。这两个群体之间需要不断地交流。
获得诺贝尔奖后,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有趣的是,获奖对我的影响,可能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大。因为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人们对你的研究只会有两种态度——赞赏或否定!还是那些同事,还是那些科学问题。但有一件事变化很大,那就是你成了学术代表人物,要承担更多相应的职责。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Nature Portfolio”。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