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奇特的量子效应中,量子纠缠或许是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在通俗读物中,它常常被描述为“两个微观粒子存在某种关联,无论它们距离多远,一个粒子的性质发生变化,另一个能瞬间‘感知’到它的状态从而发生变化。但并没有违反相对论”;这一现象被爱因斯坦称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爱因斯坦的这句话甚至成了量子纠缠最著名的标语。关于量子纠缠的探索起源于爱因斯坦和两位合作者发表的一篇著名的关于探讨量子力学完备性的论文,后来被称为EPR佯谬。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约翰·贝尔(John Stewart Bell)提出了贝尔定理和贝尔不等式,使EPR佯谬成为了一个可以实验检验的问题——量子是非定域性的吗?
本文的原标题是《并不存在什么“幽灵般的超距作用”》(There is no‘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这是因为爱因斯坦是从定域性考虑的,而如果我们认定量子的非定域性,纠缠就不是真正的“作用”,这种反直觉正反映了量子的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最大差别。数十年来,为了检验量子的非定域性,物理学家在贝尔的基础上找到并填补了各种检测的漏洞,而量子力学一次又一次通过了考验。量子纠缠是存在的,但我们今天仍不能完全理解量子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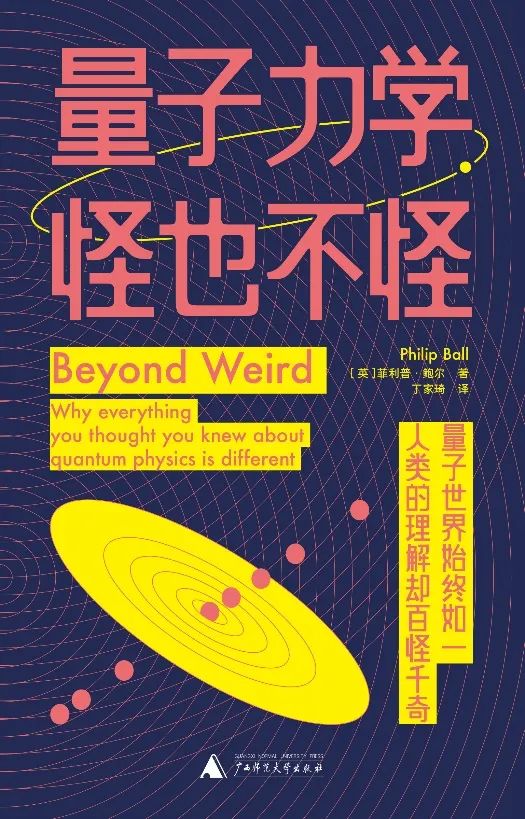
本文经授权摘自《量子力学,怪也不怪》(Beyond Weird:Why evergthing you thought you knew about quantum physics is different,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标题为编者所加。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购买此书。点击“在看”并发表您的感想至留言区,截至5月8日我们会选出一条留言,赠书一本。
撰文丨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
翻译丨丁家琦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真实”,同“波”和“意识”一样,也是人造的词语。我们的任务则是学会正确地,也即毫无歧义且连贯一致地使用这些词。
——尼尔斯·玻尔
激光,探索量子力学的最强武器
可以说,量子力学在当代的复兴始于20世纪60年代,约翰·贝尔提出关于量子纠缠的实验的时候。但就如20世纪最初几年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建立量子力学本身的时候一样,整个世界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跟上来。
而在这场量子力学复兴中,爱因斯坦依然功不可没,尽管方式比较间接。1917年,他指出,根据被能量激发的原子发射出的光的量子力学性质,如果有一系列这样的被激发原子,所有的光子就可能像雪崩一样一下子都释放出来,且它们的波形都完全同步。1959年,这一效应被命名为“光放大受激辐射”(light-amplified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这个累赘的术语被浓缩成易于发音的首字母缩写词“LASER”(激光)。20世纪60年代初,研究者找到了用实验实现激光的方法,首先得到了受激放大的微波,然后又得到了可见光。激光能让科学家对光子做极精准的控制,因此成为把量子思想实验变为现实的核心设备。在帮助我们突破单纯的思考,开始实际探索量子力学基础原理的过程中,它起的作用比什么都大。
到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就可以用激光来进行量子纠缠贝尔检验了。这个实验难度极高,首次尝试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约翰·克劳泽(John Clauser)和斯图尔特·弗里德曼(Stuart Freedman)。他们用激光激发钙原子,从中诱发出一对偏振相互关联的纠缠光子,并且用我在上一章描述的“四态”设置来测量两光子偏振间的EPR关联度。
克劳泽和弗里德曼发现,纠缠光子的关联度比贝尔定理中隐变量理论所允许的值要高。但他们的结果并不完全清晰,比如首先他们的实验次数就没有多到让统计结果完全有说服力。1982年,阿兰·阿斯佩(Alain Aspect)及其合作者在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做了一个更具确定性的实验,证明纠缠符合量子力学,而不符合隐变量理论。他们也用了激光和光纤技术来产生并操控纠缠的光子。
前文提到,贝尔检验需要列举粒子在不同测量角度下的关联度。阿斯佩和同事们成功补上了贝尔论证中的一个漏洞:测量光子偏振的滤光器可能(因某种未知机制)发生相互作用,从而人为增强测量到的量子关联度。法国团队可以让滤光器迅速改变方向,间隔时间短于光子从出发至到达滤光器的时间,因此另一个滤光器无论如何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影响这一个滤光器,并调整其方向设置。
这样一来,似乎量子力学的确是对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纠缠意味着什么呢?戴维·默明(N. David Mermin)说,EPR实验的奥秘在于“它呈现给了我们一系列就是无法解释的关联”。量子力学能给予我们的只有对结果的指示,但这就足够了吗?
没有幽灵,没有超距
首先,我们得直面这个“悖论”。如果粒子的属性在被测量之前就是不确定,那么似乎在EPR实验中两个粒子之间的确发生了瞬间通信。没有被观察的粒子好像立刻“知道”了对另一个粒子的测量产生了怎样的偏振或自旋,并且自己采取了相反的方向。然而,与爱因斯坦设想的相反,这不是真正的“作用”,也不是“幽灵般的”,甚至整个过程都与“距离”无关,自然也不违反狭义相对论。
相对论是说,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不可能超光速地对另一个地方的事件施加“因果”影响。所谓“因果”,意思是爱丽丝做的某件事决定了鲍勃看到的现象。只有这样,爱丽丝才能利用二人观测结果间的关联与鲍勃通信。
现在考虑博姆(David Bohm)的EPR实验版本,两个粒子的自旋相互关联。爱丽丝选择了她的观测方向(即施特恩—格拉赫自旋测量中两个磁体的相对角度),然后她的这些测量结果就与鲍勃的显示出了关联。但他们只有相互比对了对方的测量结果之后,才能推导出这一点——比对结果需要用经典的手段来交换信息,而经典手段不可能超过光速。鲍勃不可能超光速地知道爱丽丝的测量结果。
因此,虽然爱丽丝和鲍勃各自都似乎可能在一瞬间推断出某些事——你可以称之为“幽灵般的超距作用”——但他们无法利用这种幽灵般的连接来超光速地传递任何信息。我们假设爱丽丝与鲍勃的粒子是反相关的(即二者方向相反),而爱丽丝尝试利用这种关系,通过改变自己磁体的方向来瞬时传递信息给鲍勃。如果鲍勃测量到自旋向上,他不知道这是因为爱丽丝的粒子自旋向下、且磁体方向与他的相同,还是因为爱丽丝的粒子自旋向上但磁体方向和他的相反,或者因为她的磁体与鲍勃的成直角,因此他们俩的粒子并无关联。鲍勃此后的测量都会得出向上或向下的结果,但他从中无法推断出爱丽丝的磁体的情况。
等等,难道这不还是说爱丽丝通过她的选择是造成鲍勃测量结果的原因,只是鲍勃不能理解爱丽丝传递了什么信息吗?不是这样的。爱丽丝完全没有“造成”鲍勃的粒子自旋向上,因为她甚至无法把自己粒子的自旋固定下来!它可能随机地或上或下。爱丽丝并不能决定鲍勃观察到的现象:没有什么“超距作用”,狭义相对论依然完好。
但他们比对结果的时候,仍然出现了某种关联。这关联从何而来?正如默明所说,“没有解释”——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来自某种“量子性”,但我们无法将其表述出来。
虽然以上论证在科学上是合理的,但你不免会感觉我们在精神上违反了相对论,只是编造了一套逻辑上的论证来否认这一点。哪怕相对论(九死一生地)未受损害,量子纠缠还是有某种离奇的特征,因为它颠覆了我们对“这里”和“那里”的先入之见,搅乱了时间与空间。
检验非定域性的各种漏洞
科学家花了很多年才搞清楚爱因斯坦对EPR“悖论”的推理哪里错了。问题在于,量子力学中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常识,背后常常都有问题。
爱因斯坦及其同事做了一个非常理所当然的“定域性假设”:一个粒子的属性只局限在这个粒子上,而此处发生的事情必须经过在空间中的传播才能影响彼处发生的事情。这看起来完全不言自明,根本不像个假设。
然而量子纠缠颠覆的,恰恰是这种定域性,这也是为什么用“幽灵般的超距作用”这种角度来看待它完全错误。我们不能把EPR实验中的粒子A和粒子B看作相互分离的两个实体,哪怕它们在空间上是分离的。在量子力学中,纠缠让这两个粒子变成了同一物体的不同部分。或者换句话说,粒子A的自旋并不仅仅位于A这里,就像一个板球的红色局限在这个板球上那样。在量子力学中,属性可以是非定域性的,只有先接受了爱因斯坦定域性假设,我们才需要说对粒子A的测量结果会“影响”粒子B。量子非定域性的整个观念都与此不同。
其实,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其实是另一种量子叠加态。前文介绍过,叠加态指这样一种情形:对量子物体的测量可能产生两种或更多的可能结果,但我们在测量之前不知道结果会是哪个,只知道它们各自出现的相对概率。纠缠是同一个思想,只是应用在了两个或更多的粒子上:粒子A自旋向上同时B自旋向下,与正好相反的布局,两种状态的叠加。两个粒子虽然彼此分离,但一定仍然由同一个波函数来描述。我们不能把这个波函数拆解开,成为相互独立的两个粒子波函数的某种组合。
量子力学可以眼都不眨地轻易接受这种观念:写下它的数学公式就好了。问题在于如何形象化地说明其意义。
因为量子非定域性如此反直觉,科学家也花了极大的气力才证实它。会不会是我们忽略了别的什么东西,才造成了一种非定域性的错觉呢?
为了检验一个这样的漏洞,阿斯佩做了一个实验,而这只是一系列至今仍在进行的研究的开端。阿斯佩及其合作者考虑并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探测器之间存在一种很快但不及光速的相互影响,这一可能性如今被称为“定域性漏洞”或“通信漏洞”。那你可能会问,什么样的影响会有这种效果?谁知道呢,毕竟量子世界里充满了惊喜。你不试一下,就不能说哪个事情一定不可能。
如今,我们甚至可以以比阿斯佩更高的置信度排除这一漏洞。我们可以增加两个探测器(包含测量光子偏振的滤光器)之间的距离,让它们在整个实验结束之前都不能有低于光速的信号传递给彼此。1998年,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研究者把两个探测器的距离增加到400米,给先进的光学技术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在任何通信通过测量点之前就完成测量。他们发现,实验结果没有变化。
另一种是“自由选择”漏洞,即,有没有可能粒子在进入纠缠态后,其本身就被“编入了”某种定域属性,而正是这种属性在测量时影响了探测器的设置?这种可能性在2010年被一项实验排除了(实验同时也排除了定域性漏洞)。该实验确保了,探测器不仅离彼此很远,也离光源很远:光源和一个探测器分别位于加那利群岛的两个岛上。这些实验附带也证明了纠缠这类量子效应的另一个特点:它们可以跨越宏观上很远的距离而一直存在。说量子力学只关于“很小的物体”是不准确的,这就是一个原因——它在你我之间也起作用,不管你在哪里。
还有一种漏洞叫“公平抽样漏洞”或“探测漏洞”。它指这样一种可能性:粒子的某些定域属性让探测器的探测出现了偏差,因此我们的抽样不是真正随机的。在任一场贝尔实验中,探测都不完美:只有一部分粒子会被测量到。要得到可靠的结果,被测量的粒子须得真的能代表全体粒子。要排除探测漏洞,我们需要很高的探测效率,这样才能有信心地说我们观察到了粒子的全貌。
确实啊,要是目前的实验结果完全符合量子力学的预测,仅仅是因为我们对粒子的探测效率不够,一旦改善了探测方法就会看到背离预测的结果,那可就太不走运了。
但还是,谁知道呢?因此,2013年,维也纳大学的安东·蔡林格带领一个研究团队做了个实验。他们使用了一种更高效方法探测粒子(光子),捕捉到了75%的光子。对于前文所述的那类EPR实验而言,这个效率仍不足以百分之百地确定贝尔不等式被违反了,但蔡林格与同事们使用了贝尔定理的一个变体,巧妙地把未被测量的粒子可能产生的效应囊括了进去,于是,只要测量效率高于67%,就足以证明量子力学是对的。因此蔡林格等人的实验有着消除探测漏洞的能力,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
还有别的漏洞吗?要想出其他有道理的漏洞越来越难了,但如果不同的漏洞会在不同的实验里起作用呢?这还真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同样,我们还是应该检验一下。现在我们的目标是同时堵上几个不同的漏洞。2015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的罗纳德·汉森(Ronald Hanson)领导了一个团队,用一项堪称绝技的实验同时排除了通信漏洞和探测漏洞。实验使用了相互纠缠的电子而非光子,因为电子比光子更易探测,于是避开了探测漏洞。实验把电子的纠缠与光子的纠缠连接了起来,而光子可以沿光纤传送很长的距离(在实验中是1.3千米),因而也堵上了通信漏洞。奥地利的团队,还有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团队,也进行了同时堵上这两个漏洞的实验。
荷兰团队的实验结果,自然也以“爱因斯坦错了,幽灵般的超距作用是真的”这样的标题被大肆报道。但你现在知道了,情况并不是这么简单。
时空与纠缠
有科学家提出,量子纠缠反映的是跨越空间的相互依赖性,正是这一点缝合了空间和时间的结构,形成了一张“时空”网络,使我们可以谈论“时空”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关系,不过这一想法仍处于高度推测性的理论图景阶段。时空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描绘的四维结构,该理论表示它有特定的形状。正是时空的形状定义了引力:质量让时空发生弯曲,弯曲的时空导致的物体运动就使得引力得以显现。换句话说,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所支持的引力理论如何协调一致,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团,而纠缠或许正是解决这一谜团的关键。
在量子宇宙的某些简单模型里,一种看起来很像引力的现象可以只基于量子纠缠而自发产生。物理学家胡安·马尔达塞纳(Juan Martín Maldacena)已经表明,一个只有二维空间且全无引力的纠缠量子宇宙模型可以模拟的物理现象,与在充满时空结构(这是按广义相对论描述引力的必需)的三维“空”宇宙中的物理现象相同。这个描述很拗口,但它相当于是说,拿走二维模型中的纠缠,就相当于放出了三维模型中的时空。或者也可以说,三维宇宙中的时空和引力,就好像是其二维边界表面上的量子纠缠的投影。如果遍布在边界上的纠缠,时空就会被拆散,三维宇宙就解体了。
马尔达塞纳的这一理论过于简单,无法描述我们所在的宇宙中发生的情况,因此也只是很初步的。但很多研究者猜测,纠缠与时空的这种深层连接,揭示了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间的某种关联,即,如果想让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相一致,我们需要怎样改变时空观。戴维·博姆在几十年前就预见到了这一点,他提出,量子理论暗指与我们所说的时空相连接的某种秩序,但更为丰富。有些研究者如今认为,时空可能实际上就是由量子纠缠形成的这些相互连接造成的;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没这么简单。
不管这些想法如何进展,如今物理学家们越发认为,量子引力理论不能仅仅从巧妙的数学推导中产生,而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度看待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时空只是我们设定的一种结构,用来描述一个事物如何影响另一个事物,并表达这类相互作用的局限性。它是因果关系的演生属性。而如今我们已经看到,量子力学迫使我们修改关于因果性的先入观念。非定域性、纠缠和叠加态不仅让物体能完全无视空间的分离而相互连接,也产生了与时间有关的古怪现象,比如产生了时间上“反向因果”的错觉(也许不止于此?),或者允许两个事件的因果顺序发生叠加(因此哪件事先发生就不确定了)。
或许宇宙的因果结构是一个比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还更为基本的概念。我们在后文中会看到,为什么这样的因果结构可以成为从头开始重构量子力学,使其基本公理更具物理意义,同时减少其抽象性和数学性的极好出发点。
“当我从透过扇圆形窗户看这个球时,它是红色的”
1967年,贝尔提出引入量子非定域性概念的贝尔定理三年后,数学家西蒙·科亨(Simon B. Kochen)和恩斯特·施佩克尔(Ernst Specker)发现了量子力学与非定域性相关的另一个反直觉面向。他们的工作与贝尔定理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但直到最近才开始得到较多的关注(贝尔其实得到了与科亨和施佩克尔相同的理解,他于1966年就形成了证明,但发表晚于后二人)。
科亨和施佩克尔指出,量子测量的结果可能依赖于它们所处的背景。这与“针对基本是同一套的系统所进行的不同类型实验(比如同一个双缝实验有没有加入‘路径探测器’)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微妙的不同。它是在说,我们如果透过不同的窗户去观察一个量子物体,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东西。
如果你想数一个罐子里的白球和黑球各有多少,不管是先数白球还是先数黑球,是把它们排成五个一排地数还是把两种颜色的球分成两堆再分别称重,你得到的答案总是一样的。但在量子力学中,你即使问同一个问题(“白球和黑球各有多少”),得到的答案可能还要依赖于测量方法。
前文中我们看到,以不同的顺序进行测量(先测量这一项还是那一项)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这是因为,要从波函数中提取出可观测属性的值,就要对其进行数学运算,而不同测量顺序的运算是不对易的。
科亨-施佩克尔定理规定了这种对环境的依赖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从效果而言,它也是一条推论,来自:我们选择不去测量的性质会影响我们确实测量了的性质。它要探索的,就是在我们选定的用来观察量子系统的窗户外面,会有什么结果。
关于这一定理,施佩克尔讲了一个故事。一位亚述的预言家不想让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他认为不配的求婚者,因而为求婚者们设置了一个挑战。他在求婚者面前摆了一排三个密闭盒子,每个盒子里都可能有宝石,但也可能没有。关于这三个盒子装没装宝石,不管你怎么预测,都一定会有至少两个盒子状态相同:要么都是空的,要么都装了宝石(读者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一定是这样)。先知让求婚者打开自己认为状态相同的两个盒子,如果说对了,求婚者就可以娶预言家的女儿。但这些求婚者绝不会猜对!他们打开的两个盒子,总会有一个是空的,而另一个里面有宝石。这怎么能做到呢?哪怕单凭概率,也能保证某个人在某个时候猜对吧?
最后,先知的女儿等不及要结婚了,就介入了一个俊俏小伙儿的答题过程,他是一位先知的儿子。不过,她没有打开先知儿子所预测的状态相同的两个盒子,而是打开了一个他猜装有宝石的盒子,又打开了一个他猜是空的的盒子,而两条猜测都对了。预言家无力地反驳了一下,最终也只能承认这位求婚者做出了两条正确的猜测,因此把女儿嫁给了他。
之所以此前的求婚者都没能猜对,是因为这些盒子是量子盒子,预言家让它们相互纠缠、产生关联,使得一旦打开的两个盒子中有一个里面装有宝石,另一个就是空的,反之亦然。这样一来,永远都不可能有人完成预言家设置的挑战,表明自己猜对了。而女儿所做的事则是对同一个系统进行另一套测量,于是就能揭示挑战者的猜测是正确的。这表现的就是量子的“背景依赖性”(或称“互文性”,contextuality)。
与贝尔定理一样,科亨—施佩克尔定理也列出了,为了得出与量子力学的预测完全相同的实验结果,隐变量(假说性的隐藏因子,让量子物体的属性无论被测量与否,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必须是什么样子。前文提过,隐变量是定域性的:它们专门适用某一个物体,就像宏观物体的属性那样。贝尔定理提供了理论工具来评估这类定域隐变量是否能够解释实验结果——实验的结论总是不能。
对于隐变量,科亨与施佩克尔提出的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他们的定理表明,你不可能用只与所研究系统自身相关的隐变量来产生与量子力学一样的预测(例如两个粒子的属性关联),一旦给系统引入隐变量,你就必须也考虑用来研究该系统的仪器的一些隐变量。换句话说,你永远不能说“这个系统有如此这般的属性”,只能说它在某种特定实验背景下有这些属性。改变了背景,你就改变了所有的隐变量描述。
因此,你无法在任何情况下都用隐变量来描述关于一个粒子“什么是真实的”。在微观世界里,你不能像在宏观世界里那样,说“球是红色的”,只能说“当我从透过扇圆形窗户看这个球时,它是红色的”。在这些条件下,它“真的是”红色的(但也就是我们说某物“真的是”怎样的这种程度)。但说从方形窗户中看它时它是绿色的,这条陈述也同样是“真的”。好吧,可这个球“其实”是什么颜色的呢?科亨和施佩克尔认为,你无法得出更进一步的结论了。换句话说,关于一个量子物体,我们能设想出来的所有是非型命题——如它是红色的、它以10mph的速度运动、它每秒自转一次等——不可能同时都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确定答案。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了解所有方面——因为本来它们就不会同时存在。
出于某些难以理解的原因,对量子背景依赖性的实验研究比对量子非定域性的实验研究晚了二三十年。首批清晰证实了科亨—施佩克尔定理的实验直到2011年才出现。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怀疑量子非定域性与背景依赖性之间有某种联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达戈米尔·卡什利科夫斯基(Dagomir Kaszlikowski)提出,它们其实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一个更为基本的“量子本质”的不同面向,只是人们还没有给这个“量子本质”找到更合适的术语。不管它叫什么,这一本质都否定了对量子世界的任何“定域实在”描述。所谓定域实在描述,就是认为物体自身内在地拥有一些明确的、界定清晰的本质特征。在量子世界中,你根本就不能像在经典世界中所习惯的那样,说“这里的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与其他一切东西都无关”。
卡什利科夫斯基与其同事表明,非定域性和背景依赖性应该说实际上是互斥的:一个系统要么展现出非定域性,要么展现出背景依赖性,但绝不会同时展现两者。也就是说,“量子性”要么能让某系统在贝尔类型的实验中展现出超过隐变量所能给出的关联度,要么能让该系统对测量背景展现出超过隐变量所能给出的依赖度;但它不能同时做到两者。卡什利科夫斯基及其同事称这种现象为“行为单配性”( behaviour monogamy)。
那么,让量子物体在两种反直觉行为表现中二选一的“量子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只是问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理解量子力学的一项进步了——一直以来,找到合适的方法来表达一个问题,都是科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