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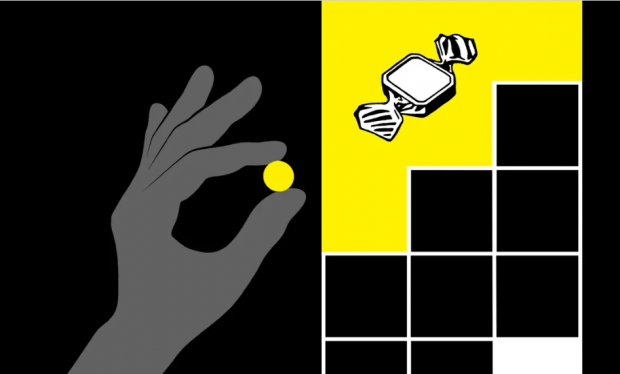
编译 | XZ
所谓安慰剂,顾名思义,通常是没有实际药效的糖片或盐水,服用之后将得到“安慰”。1955年,哈佛医学院的Henry K. Beecher提出“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这个说法,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受试者期望效应——安慰带来期望,期望好起来的人,好得更快。关于安慰剂效应的故事,在过去看来似乎是一种“欺骗”。20世纪50年代,这种效应又被称为伪药效应、假药效应、代设剂效应,即,当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无效治疗,由于非常相信治疗药物,最终症状得以缓解的现象。
过去人们认为,这种效应只有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而时至今日,有相关的研究发现,即使患者知情也有同样有效果。
今年2月12日,哈佛医学院Ted Kaptchuk团队在期刊PAIN上发表题为“Open-label placebo vs double-blind placebo for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的文章[1],研究比较了公开告知的(open-label)安慰剂与瞒着病人的(double-blind)安慰剂在治疗肠易激综合征(IBS)上的效果,结果发现两者均有效。

Kaptchuk教授表示:“在过去的十年中,一项又一项的实验均表明,公开告知患者使用的是安慰剂,能让他们感觉更好。”具体来说,Kaptchuk发现,安慰剂不仅可以缓解疼痛,还可以缓解焦虑和乏力。
随着这项结果的出现, “安慰剂是一种谎言”的说法不攻自破,一系列新的问题也油然而生。既然安慰剂也有疗效,那它能成为标准医疗实践的一部分吗?患者会愿意服用吗?从战略上来说,能用它减少成瘾阿片类止痛药的消费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会改变我们通常对医学的看法,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研究人员并没有完全确定安慰剂是如何工作的。
尴尬的安慰剂:只能保密使用
Kaptchuk回忆道:“当第一次想到给患者吃糖丸并告诉他们那是安慰剂的时候,同事们都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因为安慰剂通常需要对患者保密才能起作用。”
多年来,Kaptchuk一直试图找到让安慰剂效应更强的方法,尤其是在治疗肠易激综合征上,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慢性疾病。但一切关于安慰剂的研究对于Kaptchuk来说却是痛苦的,因为这些研究都是建立在隐瞒与欺骗上。
如果安慰剂只能秘密使用,那它永远不会成为主流医疗实践的一部分。在临床试验的背景下,患者或许能够接受欺骗,但在现实世界中,医生不能提供这种选择。
欺骗让Kaptchuk很不安。为了分析病人被欺骗的感觉,他和同事们曾对参与肠易激综合征临床试验的患者进行了一项人类学调查[2],结果发现许多人担心被施用安慰剂。病人说:“如果我服用安慰剂好了,那我的病情意味着什么?难道整件事都是我编造的?”
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消化道疾病,以反复发作的腹痛和腹部不适为主要症状,常伴有便秘和腹泻。尽管正常功能受损,但内镜、X线或血液检查看不到结构性异常。
公开使用安慰剂也有效果
既然瞒着患者使用安慰剂会让他们担忧,那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们这就是安慰剂呢?Kaptchuk觉得可以告诉患者,如果服用安慰剂后好转,那就是痊愈的迹象,并不是胡编乱造的。
2010年,Kaptchuk等人发表了一项对80名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安慰剂治疗研究[3]。他对一半患者公开给予安慰剂治疗,而对另一半患者不给予任何治疗。结果发现,比起那些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患者,使用开放式安慰剂的患者健康状况更好一些!
从这以后,公开给予安慰剂也陆续被证明可以缓解其他疾病的症状,如慢性疼痛、乏力、关节炎、焦虑症、抑郁症等。研究人员还对公开使用安慰剂的患者进行了长达五年的随访[4],结果也显示这类患者的健康状况逐步改善。
根据这些研究,Kaptchuk重新诠释了安慰剂效应。他认为,在临床背景下,患者获得康复的信心主要建立在药物给予的方式方法上。当一个人生病去看医生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治疗方式,可称为“医学戏剧”(the drama of medicine)。在这场“戏剧”中,药丸只是其中的道具,而医生则是其中的关键角色,一位具有温暖、友好个性的医生往往能产生更强的安慰剂效应。
“戏剧”的力量有多大?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Kaptchuk和他的合作者对最初80人规模的IBS患者试验进行了扩大复制[1],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最近发表的研究。这次,他们比较了三种情况:公开安慰剂(医生和病人都很清楚用的是安慰剂)、双盲安慰剂(医生和病人自己都不知道用的是安慰剂还是药)和无治疗对照组。
结果发现,在安慰剂组(前两种情况)中,70%的患者症状严重程度至少减轻了50分(按500分制分级,分数越高症状越严重),相比之下,未接受治疗的对照组中,达到这一减轻幅度的只有54%的患者。
此外,公开使用安慰剂的患者中,有大约30%报告说症状减少了150分;相比之下,在无治疗组中仅有12%。
结果还显示,在肠易激综合征严重程度评分方面,公开安慰剂组和双盲安慰剂组无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无论人们从双盲安慰剂中获得什么益处,他们也可以从公开使用的安慰剂中获得。
为什么有效?两种心理学解释
为什么开诚布公地使用安慰剂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有疗效?目前,研究人员主要从“期望”和“条件反射”两个方面来解释。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员 Darwin Guevarra说:“期望就是你相信某事会成功。”在许多研究中,期望似乎已经是设定好了的——对于那些受试者,研究人员会告知何为安慰剂效应,并告诉他们安慰剂也可能有一定作用。
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当你期望得到改善时,你可能会开始注意来自身体的各种信号,有好的也有坏的。因此,当改变期望时,你可能会选择性屏蔽大脑中发出的坏信号,转而寻找自己感觉好的信号。
但是,期望并不能解释公开使用安慰剂的全部情况。Kaptchuk说,许多报名参加临床试验的人并不真的希望安慰剂能治愈疾病,而是希望能够缓解疾病所带来的疼痛。
此时,就是条件反射在发挥作用了。经典条件反射的理论源于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用狗做的实验:当狗学会将铃声与进食联系起来,只要听到铃声就会开始流口水。对人类来说,我们可以将一件事(服用安慰剂)与积极的结果(感觉更好)联系起来。这样,即使去除了实际治疗中的药物成分,接受治疗的行为也会让你感觉更好。
在PAIN上发表的另一项研究[5]中,Kaptchuk将51名脊柱手术患者分成两组,一组接受公开使用安慰剂并服用阿片类药物治疗,另一组只服用阿片类药物进行治疗。
在实验过程中,患者在服用阿片类药物后,再服用一片安慰剂。久而久之,大脑逐渐学会了将安慰剂与真正的药物联系起来。药物通过刺激大脑释放神经递质而缓解疼痛,因此,从理论上讲,即使你只是服用安慰剂,但如果你的大脑处于条件反射状态,它也会开始释放这些神经递质。
实验结果也显示,与常规治疗组相比,那些同时服用安慰剂和阿片类药物的患者对于阿片类药物的依赖降低了30%,并且还报告疼痛逐渐减轻。
有人对这一结果表示怀疑:患者会不会只说些研究人员想听的话?但也有研究发现,公开使用安慰剂似乎确实减少了疼痛和压力的神经标记物[6]。
总体而言,研究人员仍不清楚哪种因素在安慰剂效应中发挥主要作用。但搞清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这将决定科学家设计在临床中使用安慰剂的方式。“条件反射说”似乎需要频繁的刺激,而“期望理论”可一步到位,似乎更具吸引力。
安慰剂作为药物被忽视了,也许这应该改变
Kaptchuk表示,安慰剂不是什么神奇的药丸,它或许只在特定的时候对特定的人群有效。研究表明,安慰剂(无论是否对患者公开)似乎主要作用于主观症状,如疼痛。它们对客观症状不起作用,比如骨折。
安慰剂不会缩小肿瘤,不会改善糖尿病,也不能迅速降低你的血压。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们的用处非常有限呢?
Kaptchuk认为,所有的客观疾病都有主观症状。例如,癌症是由肿瘤引起的,但也会让人感到疼痛或疲劳;还有一些疾病,如肠易激综合征,人们认为这种疾病是大脑将正常感觉误解为了疼痛,使用安慰剂或许能够干扰大脑的解读,进而缓解疼痛。
总的来说,Kaptchuk对安慰剂效应的新定义——“医疗戏剧”——是一种激进的医学思维方式,并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够认同。长期以来,主流医学对安慰剂都不屑一顾,甚至认为安慰剂效应似乎是一个障碍,需要清除它,才能确定什么是“真正的药物”。但安慰剂本身却表现得越来越像一种药物。安慰剂效应是一种额外治愈能力,它处于药物之外,或者在没有好药物可用的时候使用。
时至今日,对于安慰剂我们仍存有许多未知疑问,未来安慰剂是否能够成为一种真正的药物,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原文链接:
参考文献
[1] Lembo, A., Kelley, J. M., Nee, J., Ballou, S., Iturrino, J., Cheng, V., Rangan, V., Katon, J., Hirsch, W., Kirsch, I., Hall, K., Davis, R. B., & Kaptchuk, T. J. (2021). Open-label placebo vs double-blind placebo for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 Pain, 10.1097/j.pain.0000000000002234.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2] Kaptchuk, T. J., Shaw, J., Kerr, C. E., Conboy, L. A., Kelley, J. M., Csordas, T. J., Lembo, A. J., & Jacobson, E. E. (2009). "Maybe I made up the whole thing": placebos and patients' experiences i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33(3), 382–411.
[3] Kaptchuk, T. J., Friedlander, E., Kelley, J. M., Sanchez, M. N., Kokkotou, E., Singer, J. P., Kowalczykowski, M., Miller, F. G., Kirsch, I., & Lembo, A. J. (2010). Placebos without decepti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PloS one, 5(12), e15591.
[4] Kaptchuk, T. J., & Miller, F. G. (2018). Open label placebo: can honestly prescribed placebos evoke meaningful therapeutic benefits?. Bmj, 363.
[5] Flowers, K. M., Patton, M. E., Hruschak, V. J., Fields, K. G., Schwartz, E., Zeballos, J., Kang, J. D., Edwards, R. R., Kaptchuk, T. J., & Schreiber, K. L. (2021). Conditioned open-label placebo for opioid reduction after spine surgery: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Pain, 162(6), 1828–1839.
[6] Guevarra, D.A., Moser, J.S., Wager, T.D. et al. Placebos without deception reduce self-report and neural measures of emotional distress. Nat Commun 11, 3785 (2020).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