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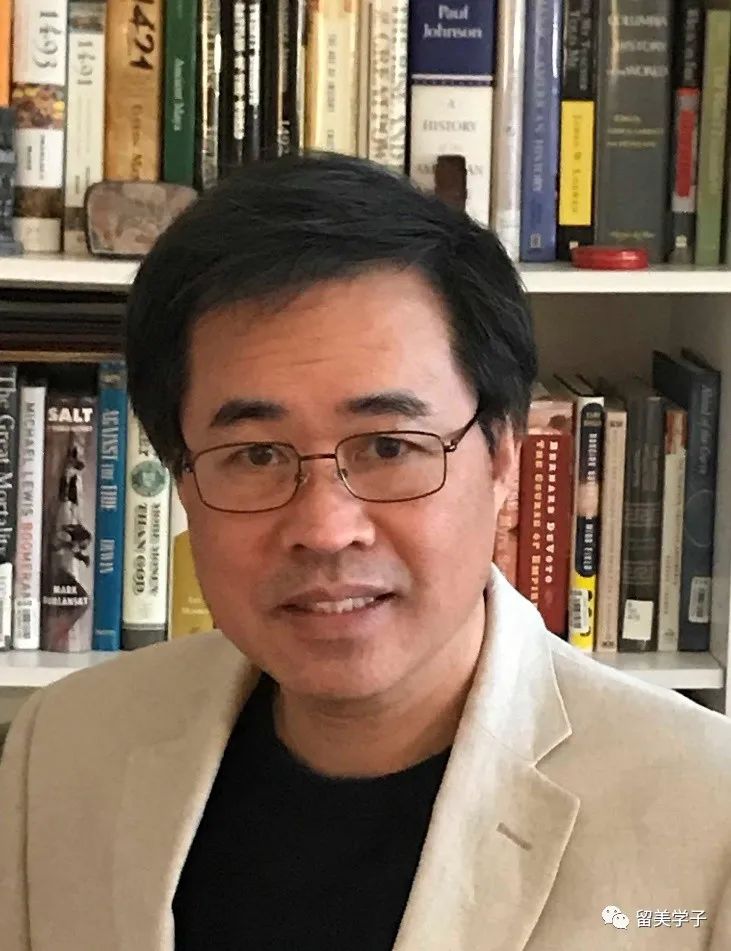
蔡维忠:理科博士,哈佛博士后,新药研发专家,现居纽约长岛。作品发表于《当代》《上海文学》《散文》《香港文学》等海内外报刊杂志,曾在美国《侨报》和《北京晚报》辟有专栏,出版散文集《此水本来连彼岸》、随笔集《美国故事》和对联艺术专著《动人两行字》,获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散文奖。
撰文 | 蔡维忠
01
我的博导
我的博士导师斯坦·珀桑于两年前新冠病毒肆虐高峰期去世,享年九十一岁。如今疫情缓和,他的遗孀乔安将一场纪念晚宴安排在宾州中部的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斯坦以前的同事、学生、博士后从美国各地赶来参加。

斯坦·珀桑
晚宴过半,在乔安主持下,斯坦的子女致辞,然后轮到斯奈佩斯博士。他是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成员,当时身材挺拔,如今快上九十岁了,驼背了,步伐缓慢了。不过,有一件轶事他讲得妙趣横生:
生物物理系被合并了。理学院院长诺利还不错,但有时做出错误的决定。对于斯坦和我来讲,一切不利于生物物理的决定都是坏决定,斯坦和我数次到院长办公室跟他交涉。
院长给我们发来备忘录,时间常常挑在星期五下午四点半左右。他的打算是,到了星期一早上,大家就会把这事忘掉。斯坦不忘。
有一次,斯坦到我办公室来,说:“这是一个很坏的决定,我们立即过去见院长,只有十分钟时间了,过后他们要走掉。”我们争来争去,院长不耐烦了,说:“做这样的决定很不容易啊,斯坦。要不你来当院长?”斯坦毫不犹疑地把手伸出去:“我接受!”我赶紧拽住他。
听到这里,听众席上爆发出一阵欢乐的笑声。
然后是我的师兄艾沙克致辞。他说:“我是斯坦的研究生。我来自印度,不认识校园里任何人,举目无亲。斯坦把我当成家人,待我如儿子。”
艾沙克讲了一件趣事:
我加入斯坦的实验室后不久,他开始跑步,并带着几个学生在校园跑。有一天,我走进米勒楼,我们的实验室在最上层六楼。电梯门打开,只见一群研究生跳了出来,领头的是斯坦。
我问:“你们在干什么?”其中一人手里拿着秒表,说:“我们要跑到楼上。”我大惑不解,事后才知道,他们要跑上帝国大厦。帝国大厦在纽约,有七十二层,纽约市刚开始一项竞赛,看谁最快跑上顶层。

纽约帝国大厦
斯坦和这群研究生在做模拟训练,从一楼沿着楼梯跑到六楼,掐下秒表,然后乘电梯下来,再沿着楼梯往上跑。他们完全不顾这样停下来再跑是否能模拟一口气跑上七十二层,乐此不疲。
听众席上又是一阵欢乐大笑。
纪念会没有肃穆的悼念,也没人正规地总结成就,不说他发表了哪些论文,培养了哪些研究生和博士后。这些资料都事先整理过,经乔安安排,贴在墙上。大家似乎都达成默契,要在轻松的气氛中怀念逝者。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艾沙克。我加入斯坦实验室那一年,艾沙克刚毕业离开,其后研究方向和我们不一样,所以在专业会议上没有碰上他,只在文献上知道他。如今,我们同席,一见如故。我不客气地请他介绍一些我不知道的往事。
“他们最终去跑上帝国大厦了吗?”我问艾沙克。
“没有,那种跑法怎么能模拟实跑!”
不过,锻炼身体的目的倒是达到了。到了我来时,斯坦还是常出去跑步,只是不再领着一群人。他终于活到高龄,看来危机感有正面的效果。
艾沙克给我讲更早的往事。斯坦成长于新泽西的一个农庄,先在海军服役,后来上大学,并在耶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专业是生物物理。他曾经破译出一个遗传密码。这事我原不知道,听后肃然起敬。
遗传密码是写到分子生物学教科书上,世世代代的生物学学生都要学习的重要发现!他被生物物理系招来当助理教授,后来升到教授。
生物物理系不大,教授们很抱团,拥戴系主任,在小王国中自得其乐。可是,从行政管理上看,一个系太小了,便是浪费行政资源。因此,生物物理系便和生物化学系合并了。原生物物理系的教授对于新系主任不满意,对于理学院的许多做法也不满意,才有他们两人跑去和院长争论的事儿。这事发生于艾沙克入学之前,斯坦大概四十多岁。
等到我入学时,微生物学系也被合并进来了,成了一个大系,分子生物学成了统合各个学科的主流。斯坦在我入学前的那个暑假为系里创建了分子生物学专题讲座,这个讲座每年举行,延续至今。
他为系里开设了分子生物学课程,我们都去修。以前的争端不再提起,但艾沙克说斯坦还是对管理层不满意。原来斯坦和很多人一样,经历了职场的不顺,但他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起。他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和智者。

师生合影,前排左四为斯坦,后排右四为作者
02
我的悼词
我讲什么事呢?
我想起选修斯坦教授的分子生物学课程时,常去向他求教。他有求必应,常常拿起一张纸或一篇科研论文的拷贝件,高高举起来指着给我讲解,而不是放在桌子上。
他的个子比我矮了不止一个头,应该是为了让我看到,才这么做的。可是,纸面与地面平行而不是垂直,他仰视看见了,我平视却看不见。他一讲解,便靠到我身边。这个动作让我觉得他可亲可近,至今都觉得如此。
我如果一边讲这个故事,一边学着斯坦仰面举着纸张的模样,估计也会引来一阵笑声。但我总觉得有些不恭敬。

毕业典礼,斯坦与作者
我选择讲另一件事。
我想起了贴在我们研究生办公室墙上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倾心于睿智的老人,美丽的女孩,和所有限制性内切酶。”
我对这三样东西印象深刻,它们构成了分子生物学研究生的理想天堂。
睿智的老人自然是斯坦(虽然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从和他第一次谈话时就有这个印象,随着其后的日常接触而加深。
美丽的女孩对于整天沉浸在实验中的研究生来说,使得生活滋润,如浴春风。限制性内切酶是做分子生物学实验的重要工具,我们用它们来切割DNA,重组基因。
幸运的是,斯坦的几个研究生都享有这三样。
纸条贴在大卫座位后面的墙上。我一直以为纸条是大卫贴的,因为他三样都有了。他在斯坦指导下,如愿拿到了博士学位,如今是一家藤校的教授。美丽的女孩是芭芭拉,斯坦雇她当技术员,专门辅助大卫做研究。他们两人每天一起来实验室,一起离开,成双成对。
艾沙克告诉我,那张纸条是他写的,不是大卫写的。
艾沙克也有这三样东西。他的美丽女孩叫海卡,是系里的硕士研究生。
有一天,斯坦开车到机场去接新生海卡,带着艾沙克一起去,给了他认识海卡的先机。他们后来成为夫妇。

笔者婚礼,斯坦与作者夫妇
我也是在斯坦的实验室期间找到了未来的妻子。在我们的婚礼上,斯坦做了一个别样的致辞:
几个月前,我听有人说,认识取决于互动的质量。这句话指的是一个人被另一个人认识的情形,也适用于一个分子与另一个分子相互作用的情形。当两个分子或两个人达到非常和谐的匹配时,会有许多接触点,每个接触点都很重要。
兰和维忠显然有很多重要的接触点。终生的友爱、分享和合作可以通过这些接触点而取得。分子和人都会随着时间变化,成长需要变化。成长会改变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点。需要保持不变的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倾听变化的信号,以便建立新的接触点。祝你们共同度过真正互相认识的一生。
斯坦特意把这些话写在纸上,在婚礼后交给我们。这张纸保存至今,想起斯坦时会拿出来看。它不仅仅是祝福,更是人生的指导。我读到关心,还读到智慧,一个有过经历的人用科学家的特殊语言写下的智慧。
03
天马行空
斯坦给系里的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开了一门分子生物学课程。他讲课的方式非常另类,每节课的前五分钟是我们听得懂的导言,其后便天马行空,一头钻进浩瀚宇宙的哪个角落,思路跳跃得让人跟不上。
他偶尔在黑板上画下几个狂草字,算是雪泥鸿爪。他指定了两本教科书,有时发个讲义,但很难找到他讲的是书上的哪一部分,或者跟讲义有什么关系。
那时我刚到美国,语言上有困难,对于他那信马由缰的授课方式,基本上没听懂。他留在黑板上的几个鸿爪,我视为珍宝,赶紧照样画下来,课后猜测是什么字,当成关键词猛查对教科书或讲义。问过几个同学,发现他们也听不懂。就这样,斯坦把那些美国同学的语言优势抹平了,就看课后谁愿意花工夫。
我至今没想明白斯坦为什么会那样奇葩地讲课。平时他和我讲课题,讲实验,从来条理清晰。他写论文,写科研资金申请,也是非常得体,否则论文怎能发表,科研资金怎能拿到?难道真的是为我抹平别人的语言优势?总之,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成绩是A。结果是好的,我毫无怨言。
虽然上他的课很费力,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另找一个教授当导师。原因是我感觉他很亲近。当然,我对于他的研究领域非常感兴趣,而且私下交流从来都很畅通无碍。
我在斯坦实验室做了五年研究,每周都有讨论交流,细节大多忘记了。只记得,他在两次重要关头为我把关。
第一次是刚开始选题,确定要建立疱疹病毒一个膜蛋白的突变体,第二次是建立一个能培养变异病毒的细胞株。我的课题是研究病毒膜蛋白的突变体,进而研究膜蛋白如何促进病毒感染细胞。这两样成功建立了,我的研究课题便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了。
如今回顾,我明白了斯坦是如何恰到好处地指导和帮助我。帮助太少了,任我毫无章法地乱试,平白浪费许多时间,学不到科学研究的真谛;帮助的太多了,等于代劳,对于研究生的成长绝对不利,即使侥幸取得了博士学位,今后也难胜任独立研究工作。斯坦所做的,不多不少,恰到好处。
斯坦做得最多的是鼓励,对于我的些小进步都给予肯定。称赞分为“好”、“优秀”、“杰出”几等,“好”以上是“优秀”,“优秀”以上是“杰出”。斯坦给我的称赞在“优秀”这一级,直接跳过“好”。这种称赞对正在经受异国文化冲击的我来说,有正面的鼓励作用。可是,他给本领域最有名的科学家的称赞是“好”。后来我弄清楚了,他对我的称赞是导师对学生的称赞,不是对同行的称赞,我还没有达到让他当成同行的高度。
有一次,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等拿到结果才告诉斯坦。那是个星期五下午,斯坦一把将我的数据拿去,回家闷头研究了一个周末,星期一回来宣布召开实验室会议,并亲自分析数据。平常没见过他替研究生分析数据的。从他过后的一些言谈,我觉得他很看重这个实验结果。他说应当找个合适的专业杂志发表,让病毒学以外的科学家也知道,后来也发表了。但是他没有为此表扬过我。
也许,这一次他把我当成同行看待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从称赞到不称赞,是一种进级,不称赞是最好的称赞。

聚会,后排左二为斯坦,后排右一为作者
04
学术孩子
乔安对我说,斯坦一直把我们这些研究生当成“学术孩子”。我觉得这个说法比“学生”更亲切,也更恰当。一个人除了有生物学上的孩子外,还有学术上的孩子,是另外一个维度的成就。
的确,我很认同他身上的许多东西,包括诚实、公平、正直、助人为乐;我从他身上承传了很多东西,包括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方法的运用。传承是怎么发生的呢,通过哪些言行,哪些事件?也许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结果吧。
如今回顾,有种无迹可寻的感觉。
不过,我记得一件事。
有一天,斯坦给我出一道有点另类的试题。其大意是,比较一些物体的大小,这些物体包括宇宙、银河系、太阳、地球、截锋(tackle)、细胞、病毒、分子。截锋是一种橄榄球队的进攻队员,而橄榄球是当时学校的品牌,方圆百十里内的居民都以为骄傲,所以试题不用“人”,而用“截锋”。
当时我觉得有些意外:我们做分子病毒学研究,要知道人、细胞、病毒、分子,为什么还要知道宇宙、星系、太阳、地球呢?
这个试题一点也不难,中学生查资料就可以回答,不该是出给博士生的问题啊。可为什么四十年的岁月把当时做过的许多试题都磨灭了,只有它还留在记忆里?原因是,它经得起思考,推敲,扩展,思路可以上达浩瀚宇宙,下抵原子之间,无边无际。
宇宙有多大?
宇宙的直径大概是一千亿光年,宇宙中大概有一千亿个星系。这样的数字是个很难描述的概念,用通俗语言就说它是个天文数字。有人说,地球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其实,地球根本够不上宇宙的一粒微尘,太阳也够不上,人体就更谈不上了。
人体难道就那么渺小吗?不妨问一个类似的问题:人体有多大?如果我们用细胞来描述,那么,一个人身上有一百万亿个细胞,这也是一个用通俗语言难以描述的天文数字。
再问:细胞有多大?一个细胞里可以装一百万个疱疹病毒。从病毒的角度衡量,细胞大得不得了。疱疹病毒够小的吧?它的体积相当于千万个水分子。从细胞的角度衡量,人体便是个宇宙。从水分子的角度衡量,病毒是个小宇宙,细胞是个大宇宙。我们把各个级别的物体比较看,宇宙中有数不清的小宇宙,小宇宙中有数不清更小的宇宙。
地球与宇宙相比太过渺小,细胞与人体相比太过渺小,把这些原无可相比的物体放在一起,发现它们都含有天文数字。天文数字便是宇宙的基本特征,每一层物体便都是一种宇宙。与天体相比微不足道的人体、细胞、病毒,在某种意义上巨大无比。
与其说宇宙中的任何物体是微尘,不如说任何微尘里自有一个宇宙。我们科学家不管研究的物体多么细微,都是在研究一个无穷无尽的宇宙。渺小的我们,便显得几分伟大。
我意识到,这道试题不是用来解答的,而是用来扩展眼界的,可以在它里边找到自己的宇宙。
这道题本身是个宇宙,出题人自然也是个宇宙。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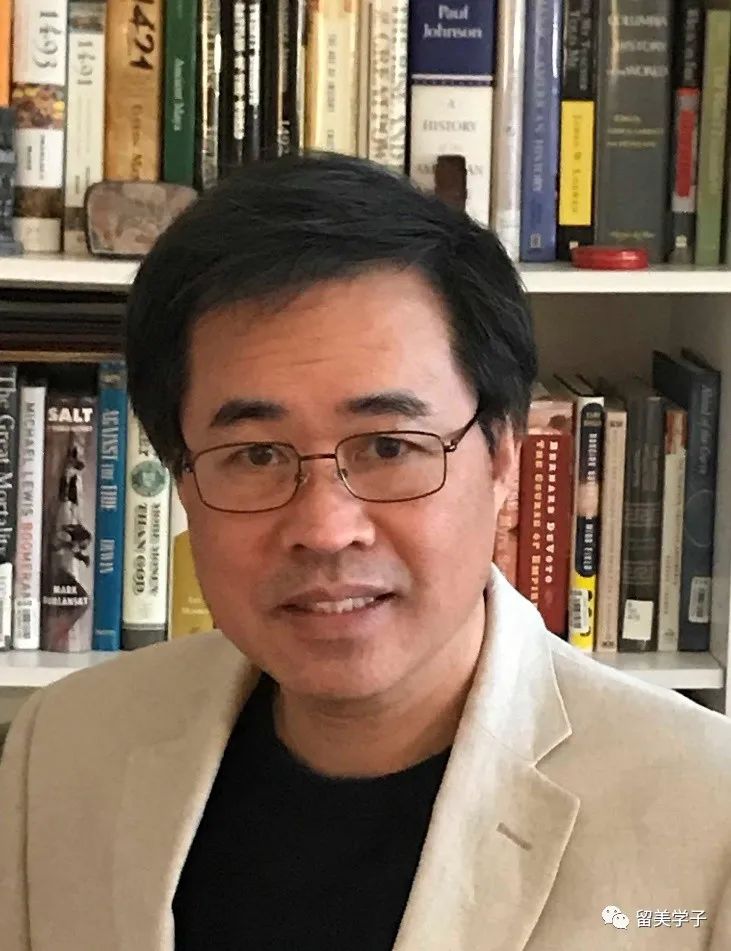
蔡维忠:理科博士,哈佛博士后,新药研发专家,现居纽约长岛。作品发表于《当代》《上海文学》《散文》《香港文学》等海内外报刊杂志,曾在美国《侨报》和《北京晚报》辟有专栏,出版散文集《此水本来连彼岸》、随笔集《美国故事》和对联艺术专著《动人两行字》,获第十二届《上海文学》奖散文奖。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留美学子”,首发于《香港文学》2023年4月号总第460期,原题《我的宇宙》。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