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类引以为傲的物理学理论,如量子力学、相对论,其实都是近似理论,它们只适用于自然世界的局部,只能描述宇宙自由度空间中的一个子集。物理学家将这样的理论称为“有效理论”,同样检验其是否成立的实验物理学,检验的也只是这个子集。
撰文 | 李·斯莫林(Lee Smolin)
翻译 | 钟益鸣
相对论、量子力学、标准模型——这些理论都是20世纪物理学的伟大发现,它们代表了物理学的最高成就。它们的数学表达十分优美,给出了精确的实验预言。同时,无数实验观测在极高的精度下证实了它们的存在。但我认为这些理论都不足以充当物理学终极理论,在它们的万丈光芒之前,这可是个鲁莽的断言。
宇宙学挑战
这些著名物理理论的一个共同特征,使得它们难以外推至整个宇宙。这些理论都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随着时间变化,另一部分则假设固定不变。前一部分正是有待研究的系统,它的自由度随时间而变;后一部分正是系统之外的宇宙,我们称它为“背景”。
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明确指出背景的存在,但它的确在那里。正是因为它的存在,前一部分世界中的运动才会有意义。即使不直接挑明,当谈论距离时,我们总是需要一个固定的参照物和一把尺子来进行度量;当谈论时间时,我们总是需要一口系统外的时钟来读取时间。
将世界划分为动态部分和静态部分是一种人为划分,在宇宙局部系统的研究中,这一划分也是极为有用的。在真实世界中,静态部分往往由系统之外的许多动态部分组成。我们忽略了这些部分的运动及演化,从而构建了一个发现简单物理定律的有效框架。
对广义相对论以外的许多理论而言,固定的背景中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几何结构。它还包含了物理定律的选取,因为这些定律同样不随时间而变。而在广义相对论之中,尽管时空的几何得到了动态描述,理论还是假设了一些固定的结构,比如固定的空间拓扑以及固定的空间维度。
当将这样的方法推广至整个宇宙时,我们遭遇了一个挑战。
要研究整个宇宙,那整个宇宙都是动态部分。而在宇宙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也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充当静态背景,没有任何固定参照物可供我们测量宇宙中的运动。
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克服这一阻碍呢?我将其称为“宇宙学挑战”。
背景独立
想要解决宇宙学挑战,我们就必须发明一个可以适用于整个宇宙的理论。这个理论中,动态个体必须通过其他动态个体来加以定义。这个理论不需要固定背景,也不容许有固定背景。我们称这样的理论为“背景独立”理论。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物理学的不断胜利鼓舞着我们可以科学地研究宇宙。此前,我们总是成功地将理论应用于一个大系统的局部。自然而然地,当面对宇宙学困局时,我们会想象宇宙是一个更大系统的局部。在我看来,这就是多重宇宙理论吸引人的地方。
当在实验室做实验时,我们会控制实验的初始条件。为了测试理论中的假设,我们会不断改变初始条件。而对于宇宙学观测而言,初始条件早已由早期宇宙给出,我们必须反推其中可能的假设。因此,要想通过牛顿范式解释宇宙学观测,我们要做两步假设:
• 假设初始条件到底是什么;
• 假设物理定律到底是什么。
普通的盒中物理学研究允许我们改变初始条件,以推导出可能的物理定律。与之相比,宇宙学中的挑战可谓难上加难。
要同时检验物理定律的假设和初始条件的假设,极大地减弱了观测的检验能力。如果我们的预言与观测不符,就存在两种更正办法:我们可以换个物理定律,也可以换个初始条件。这两个办法都能影响实验观测的结果。
这引发了新的问题,到底应该更改物理定律的假设,还是初始条件的假设?
如果我们观测星系、恒星等宇宙局部系统,我们可以通过检验许多局部系统而将检验限定于物理定律之上。同样的局部系统应受同样的物理定律管辖。如果这些系统之间有所不同,那必定源自它们不同的初始条件。可我们只有一个宇宙,因而我们无法区分哪些效应由物理定律的改变引发,哪些由初始条件的改变引发。
有时,宇宙学研究确实遭遇了这样的问题。对于早期宇宙理论来说,一个重要的测试来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CMB)。它是早期宇宙遗留下的辐射,使得我们可以一窥大爆炸后40万年时宇宙的情形。在早期宇宙理论中,“暴胀”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即早期宇宙所经历的巨大而快速的膨胀。暴胀稀释了宇宙的初始特征,将它变成我们所见的庞大却又处处几乎相同的宇宙。暴胀预测了宇宙微波背景的特定模式。它的预言和我们的观测结果非常相似。
数年之前,研究人员声称发现了微波背景辐射的一个新特征:非高斯性。这超出了普通暴胀理论的预言。(在此我跳过非高斯性的定义;我们仅需知道,这一特征可能确实存在于宇宙背景辐射之中,而标准的暴胀模型预言它不会出现。)要想解释观测,我们面临两个选项:我们可以修改理论,也可以修改初始条件。
暴胀理论也属于牛顿范式,所以它的预言也取决于理论的初始条件。
在非高斯性的观测文章发表几天之后,就有许多人撰写论文试图解释这一观测结果。有些人改了理论,有些人改了初始条件。所有这些尝试都成功预测了观测结果。事实上,人们早就知道两种方案都管用。和许多前沿的观测科学一样,进一步观测否定了最初的高斯性观测。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微波背景辐射之中到底有没有非高斯性。
在以上例子中,我们展示了让理论符合数据的两种不同方法。如果是一些参数决定了物理定律和初始条件,那么肯定有两个不同的参数都可以让理论与观测相符。观测人员称这种情况为“简并”(degeneracy)。当简并发生时,通常我们需要引入新的观测并重新做拟合,才能区分二者。但宇宙背景辐射是这个宇宙仅发生过一次的事件的余晖。面对这类观测时,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破除简并。鉴于目前我们对宇宙背景辐射的测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精度,这或许意味着我们真的无法回答到底是应该改变物理定律,还是应该改变初始条件。但是,无法区分物理定律和初始条件各自的效应,意味着当下的物理理论在解释自然现象成因时并不是那么有效。
只是近似
自牛顿时代以来一直指导着物理学发展的方法论,在我们看来已经江河日下。此前,我们认为牛顿力学或量子力学之类的理论,最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终极物理理论。我们认为,如果它们确实是终极物理理论,它们将成为自然世界的完美镜像,每一个自然世界中的真实存在必然对应于一个理论世界中的数学事实。不含时间的物理定律作用于不含时间的位形空间,这一架构是牛顿范式的基础。也正因为此,牛顿范式对于上述的镜像过程不可或缺。
在我看来,一旦我们将牛顿范式应用于整个宇宙,上述镜像真就是镜花水月了,它注定将会导致我们之前谈过的种种困惑与困局。为了验证我的观点,不妨让我们为牛顿范式中的各个理论做一次重新评估。这次评估将包括可能的终极物理理论,也将包括一些亚宇宙系统的近似描述。一些物理学家已经开始了这一评估过程。这次重新评估基于两个相互有联系的观念转变:
• 包括广义相对论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在内的所有理论都是近似理论。它们只适用于自然世界的局部,只能描述宇宙自由度空间中的一个子集。我们称这些近似理论为“有效理论”(effective theory)。
• 所有实验与观测都涉及如何截取自然世界中的局部。我们记录某个自由度子集的数据,并忽略其他自由度。然后,我们将这些观测数据与有效理论的预言进行对比。
如此看来,物理学迄今为止的成功,完全是因为它在通过有效理论研究截断过的自然世界。
实验物理学的艺术正在于如何巧妙地设计实验,将一部分有待研究的自由度从宇宙中隔离出来;而理论物理学家则针对实验物理学家研究的自然世界的局部,通过有效理论对其建模。一个真正的终极物理理论不可能是有效理论。纵观整个物理学史,我们从未让可能的终极物理理论作出预言,再与实验进行对比。
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是自然界的局部
在亚宇宙系统建模过程中,我们忽略了子系统外的一切事物,好像宇宙中就这个子系统存在,我们称这样的系统为“孤立系统”(isolated systems)。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完全孤立并不存在。正如之前我们提到的,在真实世界中,子系统与外界事物间总是存在着相互作用。从各种意义上讲,亚宇宙系统本质上是物理学家所谓的“开放系统”(open systems)。这类系统都有边界,边界内的事物与边界外的事物互动。因此,当进行盒中物理学研究时,我们将开放系统近似为孤立系统。
实验物理学家花费了大量精力将开放系统改造为(近似的)孤立系统。这类改造并不完美。
一方面,当对系统进行测量时,我们影响了系统。(对于量子力学诠释来说,这是个大问题;现在让我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宏观世界。)对每一个实验来说,并不完美的孤立系统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外界噪声的影响。实验物理学家费劲全力,试图从噪声中提取需要的数据。他们还要花费大量精力说服同行和自己:他们确实将噪声降到了最低,并从中看到了信号。
外部环境中的振动、辐射以及活跃其中的各种场,可能污染我们的实验系统,我们必须将它们隔离。对许多实验来说,能做到这一步已经足够了。对某些非常敏感的实验来说,落入探测器的宇宙射线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影响。为了屏蔽宇宙射线,这些实验的实验室通常架设在地表数公里之下的矿井中。太阳中微子的发现,就属于这类实验。太阳中微子实验将其他所有背景噪声降至可控水平,只让中微子通过。但我们目前尚未发现能够屏蔽中微子的方法。在南极的冰立方实验中,深埋于冰层下的探测器记录到了自北极而来的中微子。这些中微子纵贯了整个地球。
或许你确实可以建造一座星际尺度的厚墙来屏蔽中微子,但仍然有一种东西能轻松地穿过这道屏障,这便是引力。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东西可以屏蔽引力,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引力波的传播。因此,完美的孤立系统不可能存在。我在攻读博士期间发现了这个重要观点。
当时,我想设计一个盒子,让引力波在其中来回振荡。可引力波总能穿透盒子的壁,我的尝试屡屡失败。为了反射引力波,我便想象不断增加壁的密度。但在我达到所需密度之前,致密的壁就已经坍缩成了黑洞。我反复思量,试图寻找其他办法,最终却一无所获。我意识到这道我无法跨越的障碍本身就是个有趣的发现,甚至比我最初的设想要有趣得多。经过更为缜密的思考,我借由几个简单的假设证明,不存在可以屏蔽引力波的厚墙壁。这一结论对任何材质、任意厚度的墙壁都成立。证明过程中所用的假设就只有两条:一是在广义相对论中,物质所含的能量总是为正;二是声速总是小于光速。
以上论述表明,无论是从原则上来说还是从实际操作中来说,自然界中的系统都无法摆脱系统外宇宙的影响。这一结论非常重要,值得上升为一个原则,就让我们称它为“孤立系统的不存在性”(principle of no isolated systems)。
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们相信,所谓孤立系统仅仅是开放系统的近似:我们无法预期针对系统的随机破坏性干扰。我们可以预期噪声、测量噪声、降低噪声,但外部世界对系统的破坏可能比噪声要糟得多:坠毁的飞机可能撞进实验室,地震可能震倒实验室,小行星可能撞击地球,地球可能被一片飘过的暗物质云拉向太阳,地下室的电闸可能发生意外导致整个实验室断电……在这个庞大的宇宙中,能破坏实验进程的突发事件不计其数。当我们设计实验,并将其作为孤立系统考虑时,实际上是将以上可能全部排除掉了。
想要把这种种可以摧毁实验室的外部因素一并考虑在内,我们需要对宇宙整体进行建模。在实际建模或计算过程中,我们肯定不会去考虑这些可能性,否则我们什么研究都做不了。而不去考虑这些可能性,原则上就意味着我们的物理构建于某种近似之上。
有效理论本质上是近似理论
物理学中的主要理论,都是研究局部自然世界的模型。这些局部系统,正是实验物理学家能够制造的对象。当理论学家发明这些理论时,都将它们视作是这样那样的终极理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论学家终于意识到它们只是有效理论,只能描述宇宙中的一小部分自由度。
粒子物理学为我们提供了有效理论的极佳范例。到目前为止,实验粒子物理学家试图在极小的尺度上探索终极物理。目前,这一纪录由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保持,LHC的最小可探测精度达到10^-17厘米。到目前为止,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与这一精度以上的实验数据都符合得很好。但这也意味着,标准模型只是一个近似模型(另一个理由是,标准模型不包含引力)。如果我们能探索更小的尺度,我们或许会发现某些标准模型以外的新现象。
根据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探测的尺度与能量成反比。想要探索某个特定的小尺度,我们需要把粒子或光子加到与之对应的能量。探测尺度越小,所需要的能量就越高。因此,我们能够探索的最小尺度决定了我们能够探索的最高能量。
然而,能量和质量是同一回事(依据狭义相对论)。如果我们的探索存在一个最高能量,就意味着比这能量更高的粒子由于过重,而不能被加速器制造,因而会被忽略。在这些被忽略的现象中,可能包含新的基本粒子,可能包含未知的相互作用。又或许它们会告诉我们量子力学的原理有问题,想要描述极短距离或极高能量的现象,我们需要对其作出一些修正。
正是由于以上考虑,我们称标准模型为有效理论,它在特定能量区间与实验观测相符。有效理论的提出颠覆了一些老掉牙的观念,比如说真理的标志是理论的简洁与优美。
我们不知道在更高的能量上到底潜伏着什么现象,在更低的能量上,许多高能假说都能和这个或那个有效理论相容。因此,有效理论有着一种内在的简洁,它们可以通过一种最为简单、最为优雅的方式延伸至未知领域。之所以说广义相对论和标准模型优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可以被理解为有效理论,它们的美是理论有效性和近似性的产物。这样看来,简洁、优美并不是真理特有的标志,而是构造良好的近似模型特有的标志。
有效理论的提出意味着粒子物理学的成熟。年轻的我们浪漫地幻想,自然界的终极定律已经握在我们手上。在致力于发展标准模型数十年后,我们一方面非常确信标准模型在特定能区一定正确,另一方面又非常不确信标准模型是否能被外推到这一能区以外。
这是不是很像一个人的一生?当我们上了年纪时,我们会更加确信自己真的知道什么,同时也会更坦然地承认自己到底不知道什么。对有些人来说,这多少让人觉得失望。人们寄希望于物理能够发现自然界的终极定律,但从定义上来看,有效理论注定不会是终极定律。
你或许会想,一个理论怎么可能既被所有的实验所验证,却又充其量不过是某个真理的近似。那么你的科学观就太过天真了。有效理论的概念非常重要,它表达了以上矛盾的微妙交集。
有效理论也体现了我们了解基本粒子的进程。它告诉我们,物理学就是一个不断构建更好的近似理论的过程。当我们将实验推向更小尺度、更高能量时,或许我们将发现新的现象。如果我们真能有所发现,那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模型来描述它们。这个新的模型也会是一个有效理论,就像适用范围变大了的标准模型。
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新的理论往往会革命性地改变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同时又会保持旧理论的成功之处。有效理论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一点。现在我们认为牛顿力学是个有效理论,它只适应于低速、经典的物理过程。在这个区域内,牛顿力学还是一如往昔般成功。
过去,广义相对论曾被视作对自然的终极描述,现在人们也把它理解为有效理论。至少从一个方面来看,它不适用于量子领域。广义相对论充其量是某个大统一理论的近似。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截断某个更为基本的引力理论来获得广义相对论。
同样,量子力学似乎也是某个更为基本的物理理论的近似。其中一个迹象是,量子力学中的方程都是线性的。线性意味着它们产生的效应总是与原因成正比。物理学的其他领域也有线性方程,但这些线性方程都是某个更为基本的理论(尽管还是有效理论)的非线性方程(产生的效应数倍于输入原因)的近似。基于这些经验,我们应该相信量子力学也是如此。
事实上,我们目前所有的物理理论都是有效理论。人们冷静地意识到,这些理论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它们是近似理论。
我们依然可以胸怀壮志,去发明一套没有近似的终极理论。然而,历史和逻辑告诉我们,至少在牛顿范式的框架中,这样行不通。总之,尽管牛顿力学、广义相对论、量子力学、标准模型等令人敬畏,但它们都不可能通往终极的宇宙学理论。想要获得这样的理论,就必须认真考虑宇宙学挑战,设计一套无须借助近似就可以应用于整个宇宙的理论。
作者简介

李·斯莫林(Lee Smolin),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圈量子引力论创始人之一;现任加拿大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滑铁卢大学物理系客座教授、多伦多大学哲学系研究院成员。他还著有多本科普著作,如《量子力学的真相:爱因斯坦尚未完成的科学革命》(Einstein’s Unfinished Revolution)、《物理学的困惑》(The Trouble with Physics)、《通向量子引力的三条途径》(Three Roads to Quantum Gravity)等。
本文经授权摘自《时间重生:从物理学危机到宇宙的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2月版)第二幕“时间之轻:时间重生”,有删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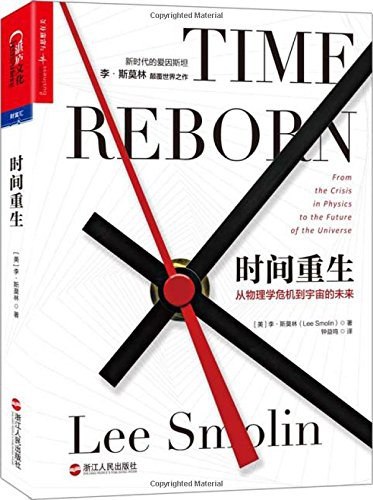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