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近日,西湖大学发布官方消息,生命科学学院迎来了首任院长于洪涛。在海外科研半生,成果卓著,于洪涛为何做出回国的决定?为何来到西湖大学出任院长?他又抱有怎样的理念和愿景?12月13日,《返朴》受邀参加了西湖大学安排的见面会,我们见到了这位低调、谦和的科学家。
采访 | 丹丽
近日,西湖大学发布官方消息,生命科学学院迎来了首任院长于洪涛。于洪涛199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长期致力于细胞周期及基因组稳定性领域的研究。他曾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药学系终身讲席教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HMI)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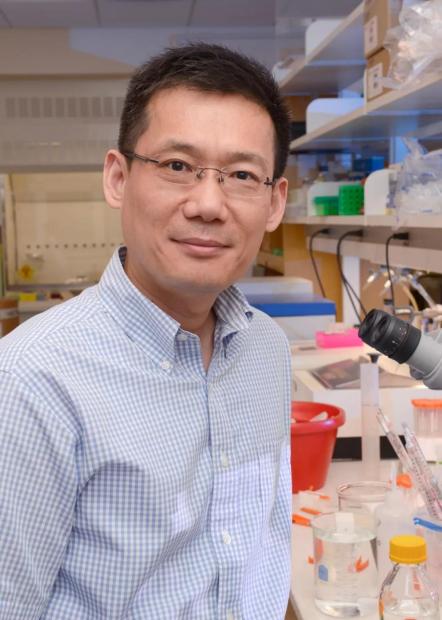
在这次瞩目的受任之前,于洪涛的名字并不广为大众所知。网上能搜到的信息少之又少,而如果打开生物医学搜索引擎PubMed,相关论文有150多篇,谷歌学术则显示他的论文被引总共近1万7千次。他曾获Burroughs Wellcome药学新研究员奖、Packard科学工程奖、白血病及淋巴瘤学会学者奖等诸多奖项,并于2012年当选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士。
1990年,于洪涛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1990年至1995年在哈佛大学师从有机化学名家Stuart Schreiber获得博士学位,期间用核磁共振的方法解析了SH3蛋白的三维空间结构。博士后期间跟随细胞生物学大家Marc Kirschner,从事细胞周期调控机理的多手段多学科研究。1999年至2019年二十年间,他受聘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药学系,历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再到Serena S.Simmons讲席教授。由于在细胞周期的调控机理和基因组稳定性等研究领域的一系列重要成果,2008年他入选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在海外科研半生,成果卓著,于洪涛为何做出回国的决定?为何来到西湖大学出任院长?他又抱有怎样的理念和愿景?12月13日,《返朴》受邀参加了西湖大学安排的见面会,我们见到了这位低调、谦和的科学家。
“我相信年轻人的看法”
去不同的地方做讲座时,于洪涛常被人问到有没有意愿要“动一动”,也就是向他发出新工作的邀请。但他坚持认为,在一个地方持续工作,具备一定基础之后,“动”一次起码要浪费半年的时间。加之对西南医学中心的环境还算满意,于洪涛一直没有选定要去什么地方。
2002年,在温哥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于洪涛与施一公相遇。两人交换了对科学的看法,谈得很投机,成为朋友后也常常关注对方的发展。2008年,两人同时入选HHMI研究员,施一公放弃名额,选择全职回到清华任教,这件事在圈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于洪涛觉得,回国的时机还不成熟。
近10年来,于洪涛经常参加国内的评审工作。每隔一两年回来看一次,他都能明显地感受到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的迅速发展,他自己的一些博后回国后也做得非常成功。“这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
2018年11月,于洪涛再次与施一公相遇,施一公向他伸出橄榄枝,请他担任西湖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于洪涛询问周围的同事、朋友,大多数人都觉得去西湖大学风险太大;而和学生、研究生聊天,年轻人却觉得西湖大学是“可以做成”的。于洪涛说:“我相信年轻人的看法。年轻人最有希望。”今年8月,他参加了西湖大学的开学典礼,目睹195位学生入学,看到这么多家长“把孩子交到西湖大学”,于洪涛终于下定了决心,完成人生中继出国留学之后的第二次大“动”。
于洪涛今年50岁了。他还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精力充沛地为国内学术界、为这些孩子们做些什么。
选人“不问出身”
于洪涛是山东淄博人,祖辈代代务农,直到父母这辈才成为知识分子。他从小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小学三年级后被父母接到城里。“我小时候在一个很小的村里面长大,当时上学,班上同学有些跟我的水平是相像的,大家考试也考得差不多。但是三年级离开后,过三五年之后再回去看,其他那些同学的发展机会要少得多。”于洪涛说,这对他而言是一次重大的人生感悟,“我现在看,大家都是有天分的,关键是有没有机会。我觉得应该给学生提供一个机会。”他感谢父母为自己创造了最早的机会,这也让他对社会和公平有了特殊的思考。
于洪涛招学生一般不看学生的成绩、院校背景、在哪个实验室做过轮转、导师的评价等等,而是直接找学生面谈。“五分钟、十分钟可能聊不出来,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定可以谈得出来。”于洪涛说,“我相信自己的判断。”虽然也有选错的时候,但大多数时候证明,他在实验室选人上都选对了。
实验室的学生快毕业了想进一步深造,于洪涛给他们写推荐信,发现自己不知道学生原先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有时候一问,发现是一个没听说过的学校。原来他在招学生时往往不看对方的简历。“我不去看这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是因为有时候这会造成一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尽管于洪涛自己一路名校毕业,但是他觉得出身好学校不是做学问的必要条件,“我擅长考试,但是做学问要的不是思维快捷,实际上做学问真正要的是想得深远。两个小时内可以做一张卷子,但是做学问谁能在两个小时之内要出答案?都是十年二十年。”绝大多数情况下,做科学实验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和心理调节能力很难走到最后。因此于洪涛认为,做学问更是一项综合能力。
到西湖大学之后,于洪涛开始筹备实验室,并于不久前发布了博士后招聘广告。他觉得,现在很多学生家长还是更希望孩子去国外或者国内一流大学比如清华、北大,如何说服这些家长,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在西湖大学同样获得优质甚至更适合的教育,成了西湖大学办学过程中要面对的一个重要命题。他认为,正是因为西湖大学小,才意味着每个学生受到的重视会更多。

科研评价怎样“去量化”
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一直是近几年为人关注的焦点。学术评价依赖量化指标,既推动了国内学术在国际范围内的发表和传播,也引发了一些负面效应。对此,于洪涛的看法是,比起没有任何标准,有一定的标准显然是好的;但标准完全是硬性的、定量的,比如要求学生发多少分的杂志、多少文章才能毕业,带来的压力会误导一些学生主观意愿上去忽视与结论不符的证据。
中国科研人员每年的发论文总数在世界上位居前列,但撤稿比例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地区撤稿率,这似乎暗示着同一项政策的正反两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科学要没有诚信的话,整个事业就完了。所以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底线,就是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错,但是不能主观地去出错。” 于洪涛不赞成量化指标带来的压力,在他看来,无论得出的结果是否显著,只要是认真做的,都是好的,这样才能够让大家诚实地汇报结果,学问才能做得好、做得下去。
“学生不光是做工作,也要完善自己。”做实验是一部分工作,但做完实验之后,得到了成果,还要出去讲这个成果,学生是不是能够像一个科学大家一样去给别人解释自己的研究?“能力不是在实验室天天做就能有的,要跟导师去谈,跟同行去谈,最后会培养出全面的能力。”于洪涛告诉大家,最终评比的时候,西湖大学会有一个学术委员会——通常是三位PI来听取学生的科学进展,再做出评价。
于洪涛进一步解释:一个做了许多实验工作的学生可能面临两种结果,一是证明了自己之前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可能会出很好的文章;但也有可能发现假设是不正确的,这可能就没有文章,或者将阴性结果发表在次一些的杂志上。“这种情况下学术委员会就会考虑,如果这个学生做得很细致,确实证明出这个假设是错误的,那么至少在我这里他同样可以毕业。这样就会淡化量化的(负面)作用。”
除了尽力排除量化指标的负面作用,于洪涛也毫不讳言地谈及他对各类“排名”的反感。他笑说,排名总让他想起《隋唐演义》的兄弟排行榜。实际上,在科学界,许多学校都在同一层次上,不可能分出一二三四;即使是不同档次的学校,也有不同专业、不同特色。学生排名、教授排名、对头衔的崇拜,都对科学发展毫无用处——说到底,诺贝尔奖是对一个人工作成果的肯定,而不是对获奖者本人的肯定。
因此,西湖大学的追求,不是引进多少千人、院士、诺奖得主,而是实质性的科研和教育工作。毕竟,国际上对一个学校的评价,不是看它有多少个某某奖得主,而是看获奖者的工作是不是在这里做的。
兴趣、创新与平等
谈科研,总绕不开创新的问题。与许多科学家一样,于洪涛也一再强调兴趣的重要性。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只有确实对一个课题感兴趣,才能享受科研的过程,才可能会有重大的突破;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如果所有人都做同样的领域,会产生不必要的竞争,浪费很多人力和物力。如果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兴趣来,一群人就能广泛涉猎各个领域——在大面积的深耕之后,必然会出现重要的新发现。
于洪涛非常强调科研的“自由度”。这不仅仅是对每个人学术兴趣的尊重,更是出于科学发展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有些时候,“我们无法评价这个工作到底有多么重要”。在他看来,唯一的要求,就是“潜心地做原创的东西”,至于这个原创到底有多重要,可能需要时间的检验。于洪涛举了Avram Hershko的例子:这位以色列科学家研究泛素十几年,开始人们都觉得这项研究没有意义,泛素的角色不过是个垃圾清理工,去除不要的蛋白,然而时间表明,泛素极其重要,几乎参与调控所有重要的分子机制和细胞活动,最终Hershko的工作获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于洪涛非常敬佩Hershko的“潜心”:“我就做这个东西,别人觉得不重要,但是我觉得重要。”
由此,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方针,就是营造“正确的”学术气氛,让年轻人自由发展,让他们“自下而上”地做科研,而不是由院级校级规划好课题。每个人跟随自己的兴趣,就相当于一个小公司的CEO,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发展,学院要做的是提供资源、平台和环境方面的支持。同时,对年轻学生的培养目标也需要“更个性化、更人性化”,“我们要培养的是下一代科学家,是人才,而不是下一步的技术员。”于洪涛坦言,这些目标完成起来“肯定比较困难”,但这也是国外比国内做得好的地方,他希望把国外“更能沉得住气、更能够潜心”的氛围在国内带起来,让大家潜心做一件事情——而不是追着热门的东西跑——做几年、十几年,做出真正的原创。
要做到这些,需要创建自由平等的环境。于洪涛希望,生命科学学院从院长到PI,再到学生、到工作人员,大家都能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平等,意味着尊重年轻科学家的选择,而不是让他们遵从学院的决定。于洪涛说:
“我们senior PI唯一的指导就是来自更多的经历,更多的经历带来不同的判断,但不一定是好的判断。因此,当一个年轻学者或学生来问我: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会讲出我认为的好处、坏处和可能出现的结果。至于最终他做出什么选择,那是他的决定。我们当然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愿望,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对方把事情分析清楚。”
在于洪涛看来,科学和工程有很大的区别:工程是可以订立目标的,技术是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资金到位,就可以在既定的时间内达成目标;而科学是无法布局的,谁也不知道重大的创新会发生在何时何地,真正的原创不可预测、无法规划。因此,西湖大学需要年轻的PI敢想敢做,再冷再偏的领域,5到10年后很可能转变成热门的领域,有重要的发现。他乐观地估计,如果有八九十个PI的体量,每个人都有原创的东西,那么一定会从中涌现出重大的科学发现。
未来:“两条腿走路”
任职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之后,于洪涛的期待是“两条腿走路”,基础研究是立足之本,只有重视基础科学才会有真正的重大突破;另外一条腿是“转化”,将研究成果推动到临床应用,促进大众健康。他表示,具体哪个方向能做出突破是无法预估的,他们能做的是招最好的人,给予平台支持,给予自由发挥的空间。在一个有风险、但有可能改变整个生命界现状的研究,和一个比较平稳的可以发文章的研究之间,他们会鼓励学生选择做有风险的研究,“即使你做不成,但有可能做出一半、20%、10%的成果,也会比你跟在别人后面跑,还是要更值得尊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于洪涛认为,教育和科研都是长期的工作,和别人比不是目的,做出对社会有贡献的东西才是目的。如果只是模仿他人的研究,即使发表了很好的文章,也未必能获得学术界的尊重。
比起国外的科研环境,中国的优势在哪里?于洪涛认为,中国人动手能力强、刻苦务实,国家投入多,经费支持力度大,这都是不可多得的优势。现在缺乏的是长期的积累,是科研质量的提升。他希望,若干年后,说到西湖大学做了什么事情,大家能够举出两三个例子——即使外行人也了解——这就是一个成功了。
版权说明:欢迎个人转发,任何形式的媒体或机构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摘编。转载授权请在「返朴」微信公众号内联系后台。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