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库恩和保罗·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家并不探求真理,因为根本不存在真理这种东西;布鲁诺·拉图尔和他的建构主义者-相对主义者同伙认为科学家制造事实,而不是客观地研究事实;米歇尔·福柯认为”科学是另一种政治“,然而,《搞科学》要恢复这样一个经典观点——科学研究是要探索原始的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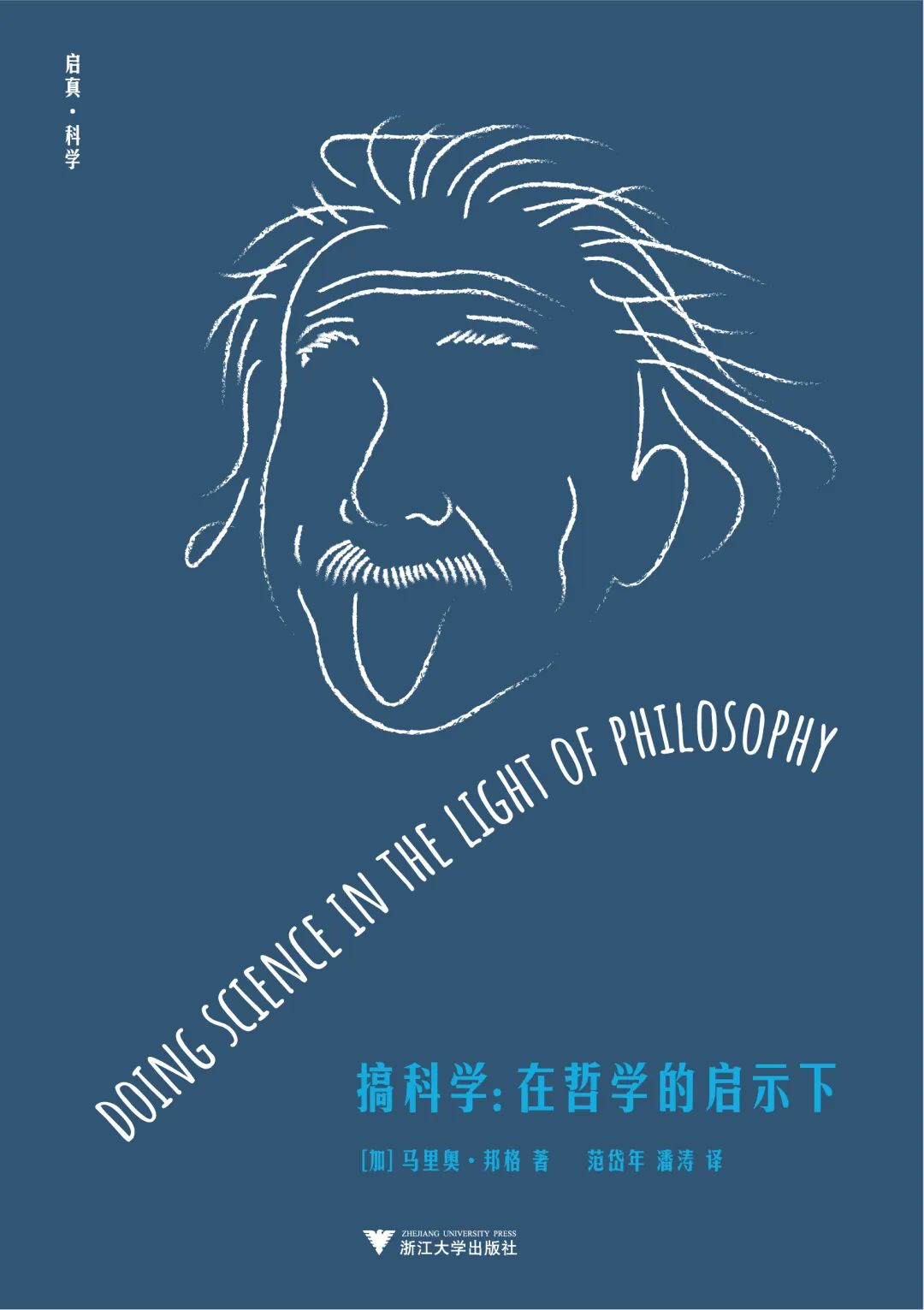
《搞科学——在哲学的启示下》(马里奥·邦格著,范岱年、潘涛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
本书的原创性在于它逆转了所有当下哲学学派的倾向,在他们那里哲学同形而上学是分离的,并与科学相隔绝。而邦格的主张是,一切知识领域的实践者都需要采纳适当形式的形而上学,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科学研究的成果。——《马克思与哲学》
撰文 | 马里奥·邦格
来源 | 《搞科学》导言
本书聚焦发展过程中的科学(science in the making),以及它的哲学前提,诸如合理性、实在论,等等。虽然这些前提大多是隐含的,很容易被忽略,但实际上它们却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有些前提有利于科学研究,而其他的一些前提却阻碍科学研究。例如,主观主义导致顾此失彼和无控制的幻想,而实在论鼓励我们去探索世界并检验我们的猜想。
我们在学校和教科书中学到的一点科学是完成的产品,而新近的科学研究计划的成果则发表在只有专家阅读的期刊上。例如,仅美国物理学会就出版了十九种有同行评议的期刊。普林斯顿大学有位著名的科学哲学教授偶然访问了美国物理学会,惊奇地发现世界上不止有一份物理学期刊。显然,他不参阅科学期刊。
科学期刊发表原始报告、综述论文,以及短讯。科学家的等级大致是以他在有很大影响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来度量的——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标准,正如加西亚(John Garcia)(1981)轰动一时的实验所表明的那样,它把研究质量同作者所在的学术机构的威望混合在一起。有些期刊有很高的标准,它们在十多篇来稿中只发表一篇。大众媒体往往只传播一些有关少数杰出论文的谣言。
显然,仅靠阅读权威科学期刊上新近的论文并不足以训练出富有成果的研究者。发展中的科学只有通过做某种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或重复这种研究才能学到,即令如此,人们还必须穿透围绕科学的神话厚层。例如科学与技术的混淆,或者甚至科学与追求权力的混淆(一个代表性的样本,可参见Numbers & Kampourakis 2015)。
让我们看一看,例如,科学思想同自由幻想的差别。确实, 无节制的幻想属于文学、艺术和神学;同样确实的是,没有幻想的、像科学那样严格的工作,例如,烹调、缝纫,或者按照既定规则的计算,是一种更加单调的工作。
幻想——超越明显的东西或陈腐之见——是创造性工作的本质,不管是在科学、技术、艺术、文学、管理或日常生活中,都是这样。可是,我们不能被这种类似性引入歧途,因为科学家寻求真理,而在其他领域里,则不要求这样。
由于幻想在科学中的重要性,19 世纪德国大学的管理机构习惯于把数学家同神学家放在一个部门里。当然,在这样做时,它们忽视了数学家与神学家的不同,数学家花大部分时间来证明猜想,而不是来做出猜想。但是,证明只能在猜想之后,而且没有提出新假说的规则:没有发明术(ars inveniendi)这种东西。
另一个流行的错误是科学与人无关。这一点说的是,与爱情和滋味不同,科学研究是与个人无关的,人们倾向于说, 科学程序和成果是可理解的,并且符合客观标准的评价,诸如原创性、明晰性、精确性、逻辑一贯性、客观性,同以往知识总体的相容性、可重复性,属于公众领域而不是私人的宗派的领域。
但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当大学开始分为系而不是讲席时,讲席教授们的行为就像封建君主,他们中的某些人要求拥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在20 世纪60 年代,当西欧大学重组为系时,海德堡一位著名的教授名为M-L,拒绝并入系内,在他的门上挂了一块板,上写M-L 领地。而在一所西班牙大学中,一位量纲分析—— 应用数学中一个很小的没有活力的部门——的专家,自己成立了一个系——一个人的量纲分析系。
说到科学- 哲学的联系,例如,谈谈第二性质(qualia)的研究,诸如颜色、滋味和气味。当我在20 世纪30 年代上中学学习化学时,就背诵我们在教科书中学到的各种物质对感官的影响的性质,但从未处理过。例如,我们学氯气,它看起来是黄绿色, 味道酸辣,有一种使人闷塞的气味,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在实验室中有用,但对理解化学没有多少好处,不如学会去除实验服的污点。
大多数哲学家都向我们保证,既然所有这些第二性质都是主观的,它们都不能用科学来说明。确实,正如伽利略(Galileo) 在四个世纪前在《试金者》(Il saggiatore,1693)中所教导的, 科学(那时意指力学)只探讨第一性质,诸如形状、重量和速率。甚至在今天,第二性质的存在,时常用来拒绝唯物论(通常同物理主义相等同)。
那些哲学家要是知道了今天那些第二性质已被分析为大脑的某些亚系统的第一性质,可能会感到惊讶(参见,例如,Peng et al. 2015)。这项研究是认知神经科学家做的,他们利用脑成像技术,已制成“哺乳动物”(实际上只是鼠科)的脑的味觉性质的滋味图。
特别是,他们已把滋味放在脑岛——一个处在大脑皮层下面靠近眼睛的器官。他们已经知道甜和苦的感觉相距只约2 毫米。这种第二性质不仅可以用食物消化来激发也可以用光刺激或注射某种药物来激发。尤其是,不用读天性论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或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的著作,老鼠可以训练到克服天生的爱好——喜爱甜的刺激胜过苦的刺激。
所有这些研究都预设了唯物主义的(虽然不是物理主义的) 假说作为前提,即一切精神的东西都是大脑的。今天,大部分心灵哲学家都偏爱三种心灵哲学,即唯灵论、心理神经二元论和计算机主义,如果研究者被束缚于这些心灵哲学,他们就不可能接受唯物主义。
最后,当代对第二性质的科学研究并不是哲学→科学起作用的唯一例子。事实也表明,出现了反向作用的例子:某些科学发现能够迫使某些哲学的变化——在这个例子中,唯物主义扩大到包括主观经验及其客观研究,甚至是对自由意志的研究(参见附录1)。
更精确地讲,作为机械论的古代唯物论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希腊和印度,现在只是科学唯物论的很小的一个分支,它能够影响所有科学学科,只要它能说明精神的东西而不是否定它。例如,流行的主张认为,意向性与因果性根本无关,当知道意向性是前额大脑皮层中的过程时,这种主张就消失了。
几乎上述所有的例子都属于科学哲学。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太尊重这个学科。因此,理查德·费恩曼(Richard Feynman)有一次把物理学哲学对物理学家的用处比作鸟类学对鸟的用处。
对此,人们可以回答,科学家不能回避哲学,当他们对某种假想的实体或过程的真正出现或可理解性感到惊奇时,就是如此。例如,建造和资助像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费米实验室和杜布纳的那些巨大的粒子加速器时,争论的焦点却正是发现理论家所想象的某种实体或过程是否是真实的(参见 Galison 1987)。
尤其是,如果费恩曼曾对哲学有某种重视的话,他就不会混淆定律(客观的模式)与规则(做事的规定);他就不会假设正电子是走向过去的电子;他会把他自己著名的费恩曼图看作记忆的手段而不是真实轨迹的描述;他也就不会写出如下的话,“既然我们能写出任何物理问题的解,我们就有了一个能自我支持的完备理论”(Feynman 1949)。
费恩曼可以把哲学摔在一边,忽视有关实在论的玻尔- 爱因斯坦争论(Bohr-Einstein debate),并宣称“没有人理解量子力学”,因为他选择去做许多很艰难的计算——这项任务不要求哲学的承诺。此外,费恩曼是在物理学的一个成熟的分支内,即在电动力学内工作。这个学科是一个世纪前由安德烈- 玛丽·安培(André-Marie Ampère)开创的,他在1843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论科学哲学的著作。
与此相对照,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知道他开创了一门新科学,他必须保护它,使它免受保守机构的攻击。这就是他为什么在公众场合带上正统哲学的面具,而只对少数亲密朋友,或在他的私人笔记M 和N(Ayala 2016;Gruber & Barrett 1974)中,我们看到了达尔文的唯物论的心灵哲学(在1838 年!)和非经验论的知识论。
特别是,达尔文认为——同英国的经验论者的教导相反——每一种有用的(非平凡的)科学观察都受某种假说的指导。这些哲学异端似乎帮助达尔文构思了他的科学作品,而且首先实现了他揭示生命之树的宏伟目标。
作者简介
马里奥·邦格(Mario Bunge,1919-2020),物理学家、哲学家,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通晓西班牙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1952年获物理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66年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任教授,1992年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士,2014年获颁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复杂性思维奖。他一生共写了500多篇论文和120多本书,其著作在科学哲学圈有很大影响力,代表作为《基础哲学论》。
目录
导言
第一章 太初有问题
第二章 科学研究计划
第三章 成果的评价
第四章 科学与社会
第五章 公理系统
第六章 存在
第七章 实在检验
第八章 实在论
第九章 唯物论:从机械论到系统论
第十章 科学主义
第十一章 技术、科学和政治
附录1 摆脱自由意志:一种神经科学的视角
附录2 心灵哲学需要一个更好的形而上学
参考文献
索引
译后记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