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科学史和物理学教授彼得·加里森的学术生涯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时刻。上世纪70年代末的科学史研究并不注重实验(室)本身,只将其作为一种理论诞生的附着品。而他本人对实验与仪器更感兴趣,这让他重新思考爱因斯坦。因为爱因斯坦在专利局从事的是一份务实的专业工作,而非他后来更被人熟知的抽象世界的形象。爱因斯坦得到相对论,真的是纯粹的思维结果吗?为什么他会用火车与观察者的同步作为比喻呢?事实证明,爱因斯坦并非只是比喻,思考协调时钟这一技术性问题的也并非只有爱因斯坦一人——甚至这是19世纪末的一个产业,其中也有另一位伟大的全才型学者庞加莱的身影。他与爱因斯坦将“同时性”的概念从技术与哲学的层面带入了物理学的核心地带,在这三重作用下,人类文明被彻底改变了。
撰文 | 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
编译 | 1/137
“我感兴趣的是弯曲光谱的边缘,使抽象和具体直接碰撞。”
——彼得·加里森
真正的时间永远不会仅仅通过时钟来揭示——牛顿对此深信不疑。即使是钟表大师的杰作,也只能提供绝对时间的苍白影子,绝对时间不属于人类世界,而属于“上帝的感觉”(sensorium of God)。潮汐、行星、月亮——牛顿相信,在单调的、永恒流动的时间之河的宇宙背景衬托下,万物皆变。在爱因斯坦的电子世界里,除非参考一个明确的关联时钟系统,否则没有这样一种可称之为时间的“处处都能听到的嘀嗒声”的容身之所,也没有办法有意义地定义时间……对于一个静止的时钟观察者(clock-observer)来说,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对运动中的观察者则不然。伴随着这一冲击,牛顿物理学的基础破裂了,而爱因斯坦对此心知肚明。晚年他在《自述》(autobiographical notes)中插入对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呼告(apostrophize),仿佛其间的几个世纪都消失了[1];在反思他的相对论所动摇的绝对时空时,爱因斯坦写道:“牛顿啊,请原谅我;你所发现的道路,在你那个时代,是一位具有最高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能发现的唯一道路。”[2]这一翻天覆地的时间剧变的核心,是一个非凡却又容易表述的思想,从那以后,它一直是物理学、哲学和技术的中心:要讨论同时性,你必须用光信号将两个时钟同步,根据光信号到达的时间进行调整。还有什么比这更简单的呢?有了这个时间的定义,相对论的最后一块拼图就找到了位置,从而永远地改变了物理学。
实验与仪器如何改变科学?
1979年纪念爱因斯坦诞辰百年时,所有这些重大事件的演讲者都只把物理学当作理论来谈论。我对此觉得十分奇怪,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一开始是一名专利局职员,对实验抱有浓厚的兴趣,却留下了如此彻底的抽象形象。我对爱因斯坦的兴趣即始于那个时期,但在爱因斯坦之外,我还对实验和理论惊人的协同方式感到好奇,着迷于工艺知识与理论物理学的巨大抽象之间的紧密结合。
多年来,我的工作一直受到抽象思想与极为具体的对象之间奇特对峙的指引。科学史、社会学和认识论于我而言紧密相连,我在科学史领域所从事的工作始终受到哲学问题的推动与启迪。例如,我对什么算作一个论证感兴趣;何为完成了一项论证?实验者如何区分真实效应与仪器或环境的人为效应?我们自认为知道数学演绎的结论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我通过计算机模拟演示了某个结果,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进行一次模拟,并展示了彗星尾部形成了岛屿,我是证明了这个结果呢,还是仅仅是开始了一个需要更多分析性的数学推导的解释呢?这些问题如今仍然困扰着各个领域。它们不可避免地既是历史的又是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们既涉及到普通的科学实践,同时又是根本性的哲学问题。可以这么说,当我选择解决一个问题时,通常是因为它被这些不同的光照亮了。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我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开始关注仪器和实验室时,在科学史研究中强调实验研究似乎还相当奇怪。大多数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热衷于表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工作余波),所有的科学都源自理论。我想这是对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一种反动,当时哲学家们坚持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源于感知和观察。无论如何,没有人认真研究何为实验室,实验室从何而来,以及它如何运作。从那时起,对实验实践的历史及其发展变化的探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大的研究领域。我不仅对实验室本身感兴趣,而且对最抽象的理论也感兴趣。例如,最近我一直在写关于弦论的文章,具体而言是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之间在试图厘清什么应该被证明时的对峙,这无疑是有史以来科学中最抽象的形式。
其实,对于每个具体的例子,我最感兴趣的是哲学问题如何启发并被科学实践所阐明,有时具体,有时抽象。我想我总是对抛开中级泛化(mid-level generalization)感兴趣,而探索最抽象和最具体的结合方式,就像在《爱因斯坦的时钟和庞加莱的地图》(Einstein’s Clocks, Poincaré's Maps)中做的那样。对于从紫外线到红外线的顺滑光谱里有什么我并不感兴趣,我希望“弯曲”光谱的边缘,使抽象和具体更直接地碰撞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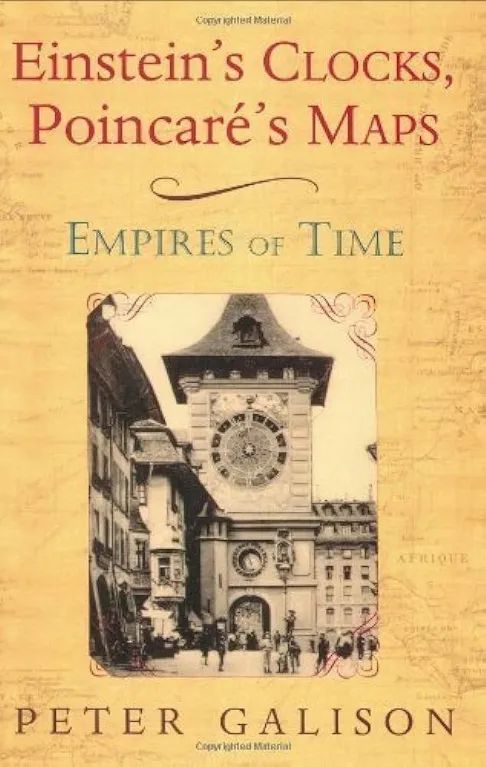
彼得·加里森所著《爱因斯坦的时钟和庞加莱的地图:时间帝国》(Einstein's Clocks and Poincaré's Maps: Empires of Time)一书。
许多年前,当我开始我的工作时,科学史几乎完全集中在思想和理论的历史上。实验与仪器,对于人们关注的议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产生理论的辅助工具。而我开始感兴趣的是某些仪器,或者说它们的使用方式,如何影响知识的运作方式以及人们提出的问题。我的第一本书《实验是如何结束的》(How Experiments End)讲的就是,无论是使用小型桌面设备还是涉及数百人的大型实验,实验人员如何确定他们正在观察的是真实的东西。
然后我转向了物理学的另一种亚文化——是一种真正对机器本身,而不仅仅是实验感兴趣的人的亚文化。我想知道某些特定设备是如何承载基本原理的。例如,像云室(cloud chambers)和气泡室(bubble chambers)这样能产生图像的机器,是如何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为一群物理学家的标准证据的?或者,像盖革计数器(Geiger counters)这样有趣的小东西——当它们靠近放射性物质时,会发出咔哒声——是如何产生一种统计上的论据的?并且让我感兴趣的是两类科学家们的传统的对照:一类想通过拍照来了解事物;另一类是计算的传统,他们想把信息更定量地结合起来,你也可以说这是数字化的,从而产生一个论证逻辑。我的第二本书《图像与逻辑》(Image and Logic)正是关于现代物理学中这两个巨大的、长期存在的传统的。
最近,我一直在研究我认为是物理学的第三种亚文化:理论家。我想要了解的是,理论家在创造最抽象的物理概念时,无论是量子场论、相对论,还是任何其他理论分支,是如何将抽象概念同现实世界非常具体的机器和设备相关联起来的。具体而言,在《爱因斯坦的时钟和庞加莱的地图》一书中,我追寻的是19世纪晚期对同时性(simultaneity)的广泛关注——时间是什么,时钟又是什么。这里还有一个关键的抽象和哲学的维度,但它也源自纯粹的技术关切。例如,你如何绘制地图或通过海底电缆发送信号?如何协调和分流列车,使它们在同一轨道上相向行驶时不会相撞?最后,我对理论家的兴趣让我开始关注19世纪末最紧迫的物理问题,即当一个物体穿过人们称为“以太”的无所不在的实体时,电和磁是如何作用的。
我对科学的物质性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我的曾祖父一直活到90多岁,他曾在柏林接受培训,后来在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osn)的实验室工作,是一名电气工程师。我和他一起在他的地下室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完全被他所做的事吸引住了。那里就是你能想象的弗兰肯斯坦博士(Dr. Frankenstein)电影中的实验室,有巨大的双掷开关,电弧闪耀于黑暗的空间中,架子上排列着装满水银的瓶子。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我17岁时离开高中,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Ecole Polytechnique)学习了一年的物理和数学。我曾有机会跟随伟大的数学家劳朗·施瓦茨(Laurent Schwartz)学习。我去过法国很多次,会说法语,之所以想去法国是因为我对欧洲政治很感兴趣——那是政治上的疯狂时期,直到越南战争结束。我想,要想在一个有趣的地方工作,唯一的机会就是从事物理方面的研究,所以我给各个物理实验室写了信。而他们接纳了我,一定是出于好玩的原因——一个17岁的美国人竟然会给理工学院写信。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哲学问题很感兴趣,认为学习物理是解决其中一些问题的途径。我在一个研究等离子体物理的实验室里工作,现在很多实验是在宏伟的实验室中的巨型机器里完成的,而当时还可以在比桌子大不了多少的设备上做小规模的实验。我对这些机器,信号发生器、记录装置、示波器,以及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是如何从这些物质实体中产生的非常着迷。在哈佛读书时,我找到了一种方法,将学习的大量的物理知识与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
这把我带回到了爱因斯坦。
协调时钟:爱因斯坦的隐喻与明示
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爱因斯坦大部分是基于他的晚年经历,那时他为自己几乎疏远所有社交和人类事物而感到自豪,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心不在焉、超脱世俗的人物。我们记得爱因斯坦说过,对于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来说,最好的事情是在与世隔绝的地方静静地守护灯塔,以便能够进行纯粹地思考。我们对理论物理学家有这样的刻板印象,并将其投射到爱因斯坦的奇迹年,1905。人们很容易认为他在专利局做一份日常工作只是为了维持生计,而实际上他真正的工作纯粹是脑力的。这种分裂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想知道他在机器和物体细节方面的工作是如何与那些抽象概念联系起来的,并开始思考相对论本身是如何与创造相对论的时间、地点和机器联系在一起。
多年以后——1997年某个夏日——我在北欧的一个火车站里,看着站台上优雅排列的时钟,分针都是一样的。我想,“天呐,他们那时造了如此非凡的时钟。多么了不起的装置!”但随后我注意到,秒针也在同步滴答作响。这意味着这些钟太准了。于是我想也许它们并不是精准的时钟,也许它们只是被电信号连接在一起,同步前进而已。也许爱因斯坦在写相对论论文的时候见过这样的钟。
回到美国后,我开始翻阅瑞士、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旧专利和工业记录,结果发现在19世纪晚期有一个巨大的协调时钟产业。突然之间,爱因斯坦1905年论文开头的那个著名比喻看起来就不那么奇怪了。爱因斯坦要求我们审视同时性的含义。他说,想象一列火车进站,你就站在这里。如果当火车驶停在你面前,你手表上的时针刚好指向7点时,那么你会说火车到达和你手表上显示的7点是同时的。但是,当你的时钟在7点时,一辆火车恰好抵达远方的车站,这意味着什么?爱因斯坦接着发展了一种技术来说明这意味协调时钟,并解释说这就是同时性。同时性的准操作(quasi-operational)定义成为他理论的基础,并导致他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即同时性依赖于参照系,由此长度的测量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是不同的。还有所有其他著名且惊人的相对论结果,都是源于这个概念。
突然间我明白了,爱因斯坦关于火车和车站的那些看似抽象的比喻,实际上完全是隐喻,但也完全是字面意思。担心“同时性”的意义的人不止一个,不只有一个与世隔绝的灯塔看守人,还有一大群人在担心“一列火车即将到达一个遥远的火车站意味着什么”。他们将电信号通过电报线路发送到遥远的车站,以此来确定同时性,这种方式与爱因斯坦在那篇改变历史的论文中描述的方式非常相似。
庞加莱的技术与工程
因此我开始进一步研究,想知道在19世纪末还有谁会担心同时性。事实证明,伟大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庞加莱与爱因斯坦的想法大致相同。他还想批判绝对同时性的概念,并让它成为一种可以衡量的东西。庞加莱没有选择火车和车站,而是选择了电报员在一条线路上交换信号作为他的关键隐喻。
在他1898年1月发表的著名哲学文章中[3],庞加莱说,同时性实际上只是信号的交换,就像两个报务员试图确定他们之间有多少经度差。如果地球是静止的,我们只要抬头看看哪些恒星正对着我们,就能找到我们的经度。但是地球在转动,所以要比较两个经度,也就是两个不同位置上方的恒星,你必须同时进行测量。因此,几个世纪以来,地图绘制者一直担心同时性问题以及如何确定它。到19世纪晚期,人们通过海底电缆跨越大洋交换电时间信号(编者注:参见《一根电缆连起欧美大陆,人类通信历史从此改变》),有趣的是,庞加莱就在其中——1899年,他被选为巴黎经度局(Bureau of Longitude in Paris)的主席。后来在1900年12月,他把他对时间的新定义从哲学和技术带入了物理学的中心地带。他表明,如果电报员在以太中移动时协调他们的时钟,他们的时钟就会“看起来”是同时的,尽管从“真正的”以太静止系来看,它们并不同时。但现在,对庞加莱来说,同时性的新定义矗立在哲学、技术和物理三大领域的核心。
庞加莱不仅是他那个时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他也是一个拥有高超工程技能的人。他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和巴黎矿业学院受训成为一名见多识广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综合理工学院最杰出的教授之一。让我感兴趣的是庞加莱的情境性(situatedness):就像爱因斯坦一样,当庞加莱援引经度测报员时,他既是在比喻,也是在字面上的。他改变了所有物理学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解决了地图绘制者的实际操作问题。
虽然远不如爱因斯坦出名,但在世纪之交,庞加莱的大众哲学著作《科学与假设》(La Science et l'Hypothèse)和《科学的价值》(La Valeur de la Science)在法国都是畅销书。这两本书对现代科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人们仍会在哲学课程中阅读它们。它们很早就被翻译成许多其他语言,包括德语和英语,并被广泛传播。庞加莱开创了包括拓扑学在内的众多数学全新领域。他帮助创造了混沌科学,我们对复杂性科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他对后来的相对论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后者在物理学的许多其他分支中也很重要。他是一个真正的全才,还继续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埃菲尔铁塔是为国际博览会而建的,庞加莱是拯救铁塔免于被拆除的人之一,因为他发现了一种把它用作军事天线的方法。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在庞加莱的指导下,埃菲尔铁塔本身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线,可以向世界各地发送时间信号——从加拿大到非洲之巅的测绘员都能靠它工作。他在高等工程和抽象数学之间流畅地来回切换,在许多领域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总是以具体、直观的方式进行推理——可以说,他是一个抽象工程师。他对时间的看法也不例外。
物理、历史与哲学的交汇
在了解了更多关于庞加莱的知识后,我试图理解他和爱因斯坦是如何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时间和空间观念的,为此我审视哲学上的抽象问题,研究物理学上的问题,以及一些技术问题(比如防止火车相撞,协调横跨帝国的地图绘制等),而这些问题可能适合整合成一个故事。它从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开始:如果我能让两个事件的时钟显示相同的结果,则这两个事件是同时发生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协调这些时钟?我从一个时钟发送一个信号到另一个,并考虑信号到达对方所需的时间。这是基本的思想,但却是相对论的所有,E=mc2,以及爱因斯坦得到的很多结果的基础。问题是,这个想法从何而来?爱因斯坦和庞加莱这两个人提出了这个实际的、几乎是操作性的同时性概念,我想把他们看作是技术、哲学和物理推理的交汇点。他们是站在这三项交叉点正中间的两个人。
有时人们问我,爱因斯坦和庞加莱关于同时性的解释的真正基础是什么?它真的是物理学吗,还是本质上是技术,抑或归结为哲学?我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的提问方式。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在问星形广场(Place de l’Etoile)到底是在福煦大街(Avenue Foch)还是雨果大街。星形广场之所以是一个地方,是因为它位于这些大街的交汇处。我们正处在一个哲学、物理学和技术交汇的非凡时刻,正是因为在世纪之交,三股非常强大的事业和推理潮流交汇在一起。这就像在一个巨大的剧院里,有三盏聚光灯同时射向同一个位置,那里就是焦点。
对于铁路工程师和地图绘制者来说,知道如何定义同时性是很重要的。对哲学家来说,弄清楚时间是什么、时钟是什么,以及如何定义时间也是很重要的:是利用机械时钟,还是利用天文现象,还是某种隐藏在所有表象背后的抽象时间。对于物理学家来说,理解什么是同时性非常重要,这样才能知道如何解释物理学中最重要的方程:关于电和磁的麦克斯韦方程。庞加莱和爱因斯坦比任何人都更关心这个交汇的所有三个部分,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一起理解。当然,时钟并没有导致相对论,就像相对论没有导致现代时钟同步的转变一样。
爱因斯坦和庞加莱极具吸引力,因为你无法想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处比这他们更相近的人了。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在许多相同的地方发表文章,在许多相同的问题上倾力研究。他们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处于顶尖地位,都喜欢为更广泛的读者写作,都被哲学家们非常认真地对待,都对技术工程有浓厚的兴趣并接受过训练。然而他们之间却远得不能再远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他来说,阅读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弗洛伊德在几个场合说过)尼采的思想(和他)太接近了,但却是围绕着另一种不同的方法组织起来的。
庞加莱和爱因斯坦各自拥有19世纪和20世纪最多的科学通信集,包括他们和其他人数以千计的往来信件,他们两人却在生命中的交集里从未交换过一张明信片。在庞加莱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们见过一次面,当时庞加莱主持一个非常重要的物理学会议中的一场,爱因斯坦在会上报告了他关于光量子的新想法。在会议的尾声,庞加莱说,爱因斯坦的报告与物理学应有的样子——即,它可以用因果相互作用(causal interactions)来描述,可以用合理的微分方程来描述,可以用原理和推论的清晰陈述来描述——如此不同,他简直无法忍受,并在做结语时明确表示,爱因斯坦所说的是如此自相矛盾,以至于可以从它得出任何事情。他认为这对科学来说是一场灾难。爱因斯坦回到家后,给一个朋友潦草地写了一张便条,讲述了同行们所做的令人惊叹的工作,他是多么钦佩甚至仰慕洛伦兹(Hendrik Lorentz),但却贬低庞加莱似乎什么都不懂。他们就像夜行船一样彼此擦肩而过,根据相对性,互相无法认可对方的存在。然而,在他们不愉快的相遇的几周后,庞加莱为正在申请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的爱因斯坦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是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信,信中大体上说,这个年轻人很可能会做一些最伟大的事情,即使他的疯狂想法只有少数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这封信极富风度和慷慨。他们再也没有直接交流过一句话,也再也没有见面。
爱因斯坦和庞加莱之间的对比,以及他们对所做事情的不同理解,代表了20世纪现代科学的两种宏大而互相竞争的愿景。尽管庞加莱和爱因斯坦对于相对论提出的方程非常相似——本质上完全相同,庞加莱始终认为他所做的是通过应用理性来校正、修复或延续过去。正如他的一位亲戚曾经说过的那样,他是在填补世界地图上的空白。爱因斯坦愿意用不同的方式,他说旧的方法太复杂了,充满了零敲碎打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的是用几条坚实的原理作为纯粹经典的基础,从头再来。庞加莱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一个帝国——毫无疑问是法兰西帝国,但也是十九世纪物理学的帝国。他雄心勃勃,但与爱因斯坦的现代主义不同,这是一种补偿性的、改良的现代主义,一种充满理性希望的第三共和的现代主义。爱因斯坦的现代主义更具颠覆性、分类性和净化性。只有通过理解哲学、物理学和技术的三重交汇,人们才能真正理解新世纪的每一个不同愿景。
科学发展的“临界乳光”
你可能会问,我也经常想知道,现在该如何看待这类事。也就是说,现在有没有这种三重交汇的类比?我是这样想的:当你考虑庞加莱和爱因斯坦时,你是在试图理解各种不同尺度下的时间协调和时钟同步(synchronization)。他们试图弄清楚如何在一个房间或天文台、一个街区或整个城市内协调时钟,与此同时,担心这些事情的人也在敷设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电缆。爱因斯坦和庞加莱不仅担心行星水平的尺度,还考虑如何在整个宇宙中的不同参照系中协调时钟。他们在问,同步是什么意思?同时性是什么意思?这些问题出现在各个尺度,从最小的到最大的,从哲学和物理直至铁路沿线的电线。从这个意义上,它不像我们在科学中提出的大多数问题,因为它没有这样的特征:从纯抽象的东西开始,然后变成应用物理和工程,最终在工厂车间结束。这不是柏拉图式的提升,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朴素版本,在其中,机器和机器车间的关系被慢慢地抽象到更广阔的领域,直到它们成为一种宇宙理论。
时间的约定俗成性问题,以及它如何与物理过程和程序等同起来的问题,是人们所考虑的所有问题中的关键。我们在实践和哲学之间来回穿梭所需要隐喻,不仅仅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凝结;(这个过程)也不是蒸发,在蒸发过程中,水变成蒸汽时密度降低。相反,更有用的是物理学家称之为临界乳光(critical opalescence)的现象。通常的乳光是牡蛎壳的颜色,你可以看到所有的颜色都被反射出来,珍珠光彩夺目的表面或某些贝壳的内表面,你可以同时看到红色、绿色和白色。物质的临界乳光发生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例如在一个由水和蒸汽组成的系统中,温度恰到好处。在这个关键时刻(临界点)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液体开始在所有的尺度上——从几个分子大小到整个系统——发生蒸发和凝结。突然之间,由于各种大小的液滴形成——从几个分子聚集到整个系统——每种波长的光都会反射回来。如果你用蓝光照射,你看到的是蓝色;如果你用红光照射,你看到的是红色;如果你用黄光照射,你看到的是黄色。
这就是我们在看待这种情况时需要用到的隐喻。庞加莱和爱因斯坦在哲学问题、物理问题和实践问题之间来回切换。在19世纪90年代末,庞加莱在读者是地图绘制者和经纬测绘员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同时他也在物理学杂志和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上发表文章。他的思维在哲学、物理和技术这三个领域之间来回切换,速度非常快。
这样一来有人可能会问,这与现在相比如何?什么样的临界乳光标志着近代的科学?在我看来,这似乎相当罕见,但你可能会在围绕计算而发展起来的科学藏品中看到它。在这里,关于意识,关于计算机如何运行,关于科学、代码和数学物理的思想都汇集在一起。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认为,意识及其器官(记忆、输入—输出、处理)是设计编程计算机的一种方式。这样被编程的计算机就成了意识的模型。在计算发展过程中被编码的信息思想,也成为更普遍地理解语言和交流的方式,并再次反馈回设备中。信息、熵和计算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成为我们的隐喻。这种临界乳光的时刻并不常见,肯定比我们所说的科学革命更罕见。它们是另一种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临界乳光指向的是科学所处的时间和地点——在那里,我们开始在完全不同的尺度上,使用并通过机器进行思考;我们在抽象和具体之间如此高频地来回切换,它们以根本性的全新方式互相阐释,而这种方式不是简单的蒸发或凝结模型可以比喻的。当我们看到这种乳光时,我们应该深入地挖掘它们,因为它们是我们文化的变革时刻。
译者注
[1]即“顿呼”,指写文章或讲话过程中,叙述某人或某物时突然撇开听众或者读者,而直接和所涉及的人或物说话的一种修辞格。
[2]原文为:“Newton, forgive me; you found the only way which, in your age, was just about possible for a man of highest thought and creative power.” 此处直接采用了许良英等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增补本第一卷,商务印书馆)中的译文。
[3] H. Poincaré, La mesure du temps,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6 (1): 1-13(1898).
作者简介

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哈佛大学Joseph Pellegrino教授、物理学教授;历史科学仪器收藏主任。加里森教授著有多部著作,例如本文中提到的《爱因斯坦的时钟和庞加莱的地图:时间帝国》(Einstein's Clocks and Poincaré's Maps: Empires of Time),《实验如何结束:意象与逻辑》(How Experiments End),《客观性》(Objectivity,与Lorraine Daston合作)等。前者获得了辉瑞科学史最佳书籍奖(Pfizer Prize for Best Book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此外他还是制片人,参与多部科学纪录片的制作。
本文编译自Peter Galison, “EINSTEIN AND POINCARE, A Talk with Peter Galison”,有删节。
原文地址:。
出品:科普中国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