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塞巴斯蒂安·怀特(Sebastian White)计划撰写“费米在美国:费米作为一名教师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留下的记忆”丛书。为此,他访问了费米教授过去的学生和同事,其中包括李政道、理查德·伽温(Richard L. Garwin)、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和维利斯·兰姆(Willis Lamb)等人。
李政道在1947年成为费米的博士研究生。在采访中,他提供了当年与费米接触的个人感觉。这篇采访稿虽然距今已有多年,但李政道先生对于费米如何教育学生的方法的回忆,仍然对于我们如何办好大学,如何对学生进行教育具有一定的意义。特此刊出,以飨读者。
采访人 | 塞巴斯蒂安·怀特
受访人 | 李政道
翻译 | 王垂林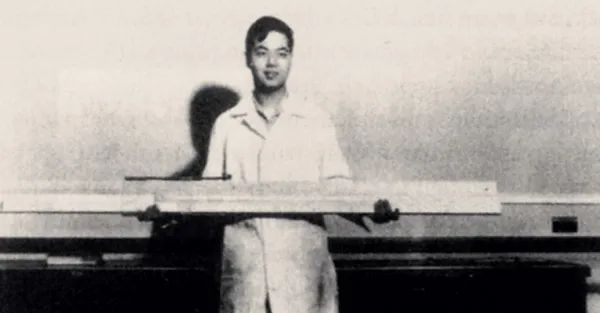
1948年,费米和李政道为计算主序星内部温度分布, 用手工合作制成专用计算尺。 怀特:你是费米40年代的研究生,有费米当你的老师感觉如何?
李政道:这是非常激动人心的经历。当然,在那个年代,芝加哥大学教授和学生整体水平是相当了不起的,再加上费米的加入。我是1946年秋从中国直接过来的。这开始了我的专业生涯。
怀特:你当时知道费米在那儿,这也是你来芝加哥的理由之一?
李政道:是的,这是理由之一。另外一个理由是因为我只有两年大学学历,而芝加哥大学是仅有的可录取我直接进入研究生课程的学校。
怀特:你是如何与费米商定你的博士论文题目的?
李政道:实际上,在当年我与费米曾经有过几个题目。第一个题目与费米关系较小,受到当时的物理研究的进展的影响较多。
那是在1948年,杰克·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er)是我的同学。他做了一个关于mu介子(现在名称为缪子)衰变的实验,发现了它具有一个连续谱。杨振宁、马歇尔·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和我分析了三个过程:mu介子衰变、mu介子俘获,和β衰变。我们非常高兴地发现它们的耦合常数大致相同。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费米的学生了,当时这一切发生得太快。杰克·斯坦伯格已经作出存在一个连续谱的实验结论,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计算这个谱,这就是我被牵涉进去的原因。他过来问我,我用三体衰变理论做出来了(自然,这计算也是基于费米的弱作用理论)。
在这个基础上,我与杨振宁和罗森布鲁斯合作,我们一起计算了这三个过程。之后,我告诉了费米这些计算结果,他很感兴趣。他说,“你们必须将这些写出来”。我说,问题是为什么它们必须具有相同的耦合常数。我认为,这里面肯定隐藏着像广义相对论那样的最根本原理。我当时非常自觉地应用费米的β衰变理论。我问他,为什么他当初的β衰变理论使用字母G代表β衰变耦合常数,他告诉我,的确,在他的脑子里含有广义相对论的想法。
之后,几个月过去了,因为存在几点困难。例如,中间玻色子必须拥有质量,可是这质量是如何产生的?在1948年圣诞节左右,费米打电话让我去他办公室。他说他刚刚收到来自蒂欧姆诺(Tiomno)和惠勒(Wheeler)的两篇文章。
他们也分析了这三个过程,并且发现了具有相同的耦合常数。但是他们没有推测到中间玻色子。我曾经向费米提起过,我正在考虑存在一个中间玻色子的可能,但是我不能搞定不变原则。当年,还不知道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弱相互作用,因为只有费米的β衰变理论。但是一旦我们将β衰变和mu介子衰变、mu介子俘获这三个作用,一起研究:这三个不同的过程引导我们深入更进一步的思考。所以我们推测,一定存在一个中间玻色子,这个中间玻色子很重,且有一个普适的耦合常数。问题是怎么样能够将V和A两种不同的β衰变存在一种选择规则,与同一个中间玻色子耦合:因为在1948年,大家公认宇称必须守恒。
我向恩里科·费米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有同感。这就是我们没有立刻写下来的原因。但是到圣诞节时惠勒的文章到了,费米说,你们必须马上写出来。
同时,费米对我说,他会给惠勤他们写信,告诉他们,我们在几个月前已经做了这些工作。在那个圣诞节,杨振宁和罗森布鲁斯外出度假去了,因此,我匆忙地写了一篇短文,署上了三个人的名字。那是我的第一篇文章。在物理评论杂志上,它只占半页纸。文中,有一段落专门讲述中间玻色子,普适耦合,它很重,寿命很短。多年之后,我和杨振宁称它为“W”,代表Weak(衰弱)作用。
这是我第一次直接(一对一)与费米较长接触。他非常有耐心。在蒂欧姆诺和惠勒的两篇文章里,有一个校对后加上的注解,感谢费米指出他的三个学生在之前也曾经独立地有过相同的思路。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博士论文题目,因为我不清楚在这个普适相互作用所依据的原理。所以,我的第一篇文章不是费米建议的,他的作用就像是一位好朋友、给以我支持和鼓励。
我的第二个课题与玛丽亚·迈耶(Maria Mayer)的壳层模型相关。这也发生在1948年。在当时,有一篇尤金·芬伯格(Eugene Feenberg)的文章,发现了一种能够适用于复杂原子核内核子的势能。它给出了这些能级。但是这个势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违反了绝热原则。
玛丽亚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讨论了她的文章,有一堆反对意见。在报告会结束时,费米问道,为什么不考虑自旋轨道(l-s)耦合?
之后,我注意到,在下一个星期,举行了另一个学术报告会,可是报告人仍是玛丽亚,而且报告题目相同。这一次,我又去听了,玛丽亚的报告内容大有进步,已经有了最终的壳层模型了,非常漂亮的模型。在玛丽亚的文章中,她感谢费米提出准确的问题的贡献。在她的诺贝尔奖讲演时,她又一次确认费米提出准确的问题的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这个场合,她说她已经考虑过自旋轨道(l-s)耦合,正好在走廊中碰巧碰见费米,那时他们停下来讨论了幻数问题。在这个版本中,费米问到了自旋轨道 (l-s) 耦合问题,而当时她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马上作了回答。显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了,她可能有了不同的记忆。
下面,再说说我从费米那儿得到的下一个题目。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一个核子在重核中的平均自由程只有大约一个核半径或者更短,非常难于理解如何保持一个轨道使得玛丽亚的分析有意义。
当时,费米有他的执著的想法。在他的早期工作中,在氩原子或者其他惰性气体内,他注意到在一个电子轨道内有可能有很多其他电子。费米利用他的有效散射长度和Delta函数模型,这样他可以获得在一种由其他电子云提供的介质中的轨道。这与实验符合得非常好。所以他在考虑同样的思路是否能够解释玛丽亚·迈耶的幻数。
我记得当时他说过,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论文题目。他向我解释。我考虑了大约有一到两个星期。之后,他问起我想清楚了没有,我说,还没有进展。在费米已经完成的工作基础上,我无能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后来,我明白了,真正的困难来自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它不像费米电子气那样简单,它与强耦合介质有关。
费米教授很有耐心,他说 “这是有点棘手。这样吧,我们互换个角色如何?”
他说,总是有些物理问题困惑他,他想寻求答案并且学到更多东西。他建议我给他讲课。我说,我会全力以赴。
在那时,费米主要是做实验。当他录取我为他的学生时,我是他唯一的理论学生。当我首次提出请求时,他说他不想带任何理论学生的。因为当时他没有在理论方面做工作,他正在建造粒子回旋加速器。他正在测量中子—电子相互作用,等等。之后,他说,好啊,他收下了我。但是看上去,这个学生有点挑剔。
他要我读文献,然后给他上课。所以,我们每星期会面一次,一起度过一个下午。我去他的实验室去找到他,然后我们一起去他的办公室。通常,我们会讨论他在上星期提出的一个题目。那时候,他对天体物理学感兴趣,如,质子与星星碰撞的问题,与宇宙线的关联。
一开始,他问我太阳中心温度是多少。我给了他一个报告:说约一千万度左右。他问我是否自己核算过。我说,这里有光强和核心内因对流引起的能量产生的两个关联方程,所以比较复杂。当时,他再一次问我,你怎么知道这答案是正确的。我写出了方程,给他演示了能量转换的规律与温度的3.5次方成正比。而能量产生与温度的大约16次方成正比。费米说:你不能依靠别人的计算结果,你必须自己核准,才能接受。
费米建议,我们也许可以制造一个计算尺来查验一下。他帮助我制作了一个长6英尺的计算尺来解题;我还保存有与计算尺一起照的照片。他做了木匠活,我刻制并且摄影放大了log尺度的标尺。当我们制作出来后,马上就计算出来了,也许就花了一个小时。我之所以描述这些情节,就是想说明他是一位极卓越的老师,当时(1948年),费米早已被公认为物理泰斗,而我仅是由中国来美国不久的青年学生。可是费米老师不惜时间和精力,引导我,教育我。
现在回到我的论文题目。我们开始了研究白矮星这个题目和钱德拉塞卡(Chandrasekhar)的工作。当年,钱德拉塞卡极限并不是现在公认的1.4个太阳质量,而是4倍或者更大。当时并不清楚白矮星的内部组成,不清楚是氢、氦还是其他更重的核子组成的。这就会改变电子和核子数的比例。引力作用在核子上,但是抵抗塌缩的压力来自于电子。所以问题依赖于电子数和核子数之比(实际上是比的平方)。当年有一篇马尔夏克(Marshak)的文章(他正与贝特〈Bethe〉合作),这篇文章称最可能的组成成分是氢。思路是这样的,因为白矮星的密度很高,从星球的核心到表面的热流会非常的快,假如白矮星的核心温度很低,这就会使燃料燃烧变慢。这也是伽莫夫(Gamow)的想法。他们声称,白矮星是星球的诞生,白矮星可能完全是氢核子组成。
这样,当时钱德拉塞卡极限是现在公认的极限数的4倍,当我试图解读马尔夏克的和马尔夏克与贝特的文章时,我意识到他们的思考可能大有问题,同时,在他们的计算中所用到的致密物质的不透明度也是错的。
我向费米提到了这几点,他建议我给他们写一封信。所以我就给马尔夏克写了信,当时他正在怀俄明州度假。回信相当粗鲁。他说:“你是谁?”当时马尔夏克正与贝特合作,在介子理论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当然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总之,他说他会给我答复。我在信中指出了我认为的他错误之处。他给我回信说我是对的。与此同时,我再进一步考虑:白矮星的内部主要元素究竟是氢,还是氦?仔细想想,我感觉到这白矮星应该全部由氦组成,不是氢组成的。能量产生是温度的一个陡峭函数而能量输出是温度的缓慢函数。
马尔夏克与贝特发现了平衡点,但是这事实上不是一个稳定解,因为如果你稍微增加一些温度,能量产生就会急速增加,整个东西就会爆炸。所以,在费米的鼓励下,我写了这个主题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发表在天体物理杂志上。这篇文章再加上对不透明度的正确处理成为我的博士论文(我的论文后来被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内对致密物质特性感兴趣的科学家应用)。
费米与众不同。不仅在物理方面,他的成就卓越,在平时待人接物方面,也是非常和善。举例来说,他给我出了一个问题,而我回答道,我不想做,如果碰到通常一位教授,他会说:“见鬼去吧。”但是,费米不是这样,他会说:“好吧,那你来教我。”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和善。我记得当时他是非常忙的,他当年正在做实验,建造芝加哥粒子回旋加速器,等等。
怀特:伽温(Garwin)谈到过费米的超凡领导魅力。他引导人们走向他工作的方向。你与费米的关系好像有点不同。
李政道:是的,我可以举出一些例子。那时期中,我每个星期与他见一次面。而每次的讨论是一整个下午,一起交谈。我们在一起度过很多时间。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任何一位老师会做到这点。当然我的意思是说,这是相当特殊的,但是当时我太年轻,不知道自己多么运气,遇到多么特殊的好老师。
在我到达芝加哥不久,费米开了一门夜间课程,只有被邀请到的学生才能参加。非常幸运,我被邀请到了,这是很特殊的。这门课在1948年到1949年共进行了约两年。每个星期他都会布置一些问题。当时,费米正在测量中子和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说,因为中子有一个磁矩,所以你可以尝试利用量子电动力学来计算它。在下个星期我利用了玻恩近似做了计算。在费米来到之前,我和另一学生穆福·戈德伯格交谈,我们两个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之后,费米来了,问我们结果。我们给了他我们的公式。“你们用了玻恩近似?”我们回答道:“当然了,你还能用什么?”他向我们解释道,如果你用了玻恩近似,当电子进入后,它就会旋转等等。简而言之,我们对于半经典计算的有效性,讨论了人们普遍认为的看法。
取而代之的是,他使用了另外一种途径计算,得到了他的公式。结果是,当有效性范围是正确时,我们的公式就会退化到他的公式,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对于实的中子磁矩和电子,只有他的公式才是对的。当时费米计算了这个问题,因为费米也同时做了实验在测量。而且已经结束了他的测量。所以他正在考虑新的相互作用(超越电磁的作用)。
通常,只要费米宣布他已经做了,我就不再做这个问题,因为他已经导出正确的答案了。
大约在1952年,我进入高等研究院不久,穆福·戈德伯格给我打电话,那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问我,我们能否一起吃个午饭。他问我有没有看过一篇福迪(Foldy)和沃希森(Wouthuysen)文章。我说没有。他说:“看一下吧,然后再回过来考虑那个电子和中子的问题。”我看了,十分肯定,我们的公式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他们的文章中,而且这公式和费米的实验结果完全符合!我吸取了一个教训。如果你得到了一个公式,你相信你的公式是正确的,你应该将数字代入公式作一下计算,可是我和戈德伯格都没有这样做。
当费米说这就是结果,我们中没有一个会产生任何疑问他是否正确,没有一个人会再费心思将数字代入,去与他的实验对比。
怀特:伽温在之前曾经讲述过一个费米在罗马时的故事。当时,费米在一个实验室工作台上工作,似乎是出于本能,他用一块石蜡取代了一块铅块,这导致了整个系列慢中子研究工作。你能否讲讲类似这样的故事,谈一下“灵感”在理论工作中的作用,例如,在费米的β衰变理论中的作用。
李政道:谈到费米的β衰变理论,用费米自己的说法,这个说法已经见诸于出版物,当时他是在试图理解二次量子化。他不太明白泡利的工作,而同时他又对β衰变感兴趣。 我们必须认识到β衰变的特殊性,如果将它与电子发射光子情况相比较的话。电子发射光子是一个粒子进(即电子),两个粒子出(即电子和光子),而β衰变的情况是一个进(中子),三个粒子(质子、电子和中微子)出。这是相当不平凡的。所以费米认识到这必须用到狄拉克海概念,我想他意识到二次量子化是分析这种新现象的工具。 石蜡的故事也许是费米的典型特点。这方面,肯定有许多文章谈到这些了。毫无疑问,这是灵感,但是,就像大部分灵感那样,这些灵感都来自于对物性起源原理的理解深度。找这种起源就像你要从一个麻袋里面挑出一粒谷粒那样。天才就是这么产生的。但是,你必须从一个麻袋开始。我认为,石蜡这件事可能是曾经断断续续下意识地出现在费米脑子里无数次后,他才作出的一种决断。以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这太神奇了。这确实神奇,但这是人类的奇迹。
怀特:我们的谈话主题涉及面很广,在这里,我能否问一下你自己的情况?
李政道: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主要的思考模式,这就要关注自己思考重点,并且使用了曾学到的手法以达到目的。与此同时,还会得到其他的“副产品”,也许这些副产品逻辑性不强,不过可以自由联想。正是这些副产品,会突然带入到思考的主题,灵感突然出现。要抓住这些灵感,如果是学理论的,需要具备分析能力,如果是搞实验的,必须拥有需要的一切实验工具和手法。我想,这样的经验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共同。讲到费米,他是特殊的,他具有极强的将抽象的事情具体化的理论分析能力,而且他又能设计和执行极有效的实验证明。可以简而言之地说,他拥有极不平凡的天才,能将不同的、极难了解的自然现象都演变成清晰化、明朗化的能力。费米是一位极伟大的理论和实验物理巨人,他也是一位很善教导很能引人深入的超级老师。
本文由原文发表于《中国科学报》 (2012-01-18 B4 人物)。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