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为海森伯回忆其于1922年夏天在哥廷根“玻尔节”听了玻尔关于量子理论的系列演讲,并且在一次演讲之后受玻尔邀约一起爬山散步中的交谈。这次交谈对海森伯的科学生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这个回忆可以看到,当时的量子物理研究的广阔视野、玻尔和海森伯的思想方法的特色。海森伯视玻尔为其老师,从这个回忆还可以看到海森伯从玻尔这里受到了怎样的影响。例如,海森伯特意提及,玻尔的结论是靠直觉从实验中猜测出来的,而不是从理论计算中推导出来的。海森伯也正是以这种方式直觉地去感受世界、猜测现象与现象的关系,然后发展出描述现象的新概念和数学关系,在量子力学的建立过程中做出了关键性贡献。本文内容取自海森伯的回忆录Physics and Beyond:Encounters and Conversions一书 (图1)。
撰文 | 海森伯
翻译 | 廖玮(华东理工大学物理学院)
来源 | 选自《物理》2023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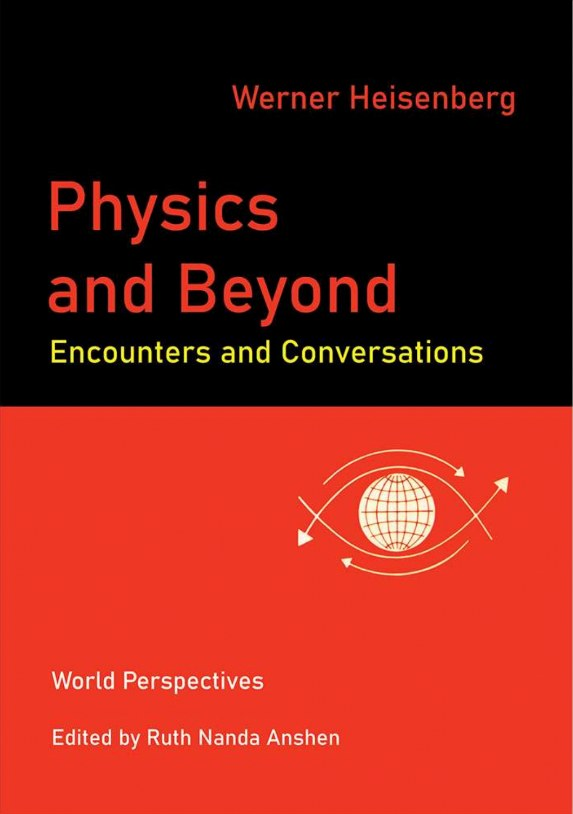
图1 海森伯的回忆录:Physics and Beyond: Encounters and Conversions,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Arnold. J. Pomerans,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1
1922年初夏,哥廷根,这个坐落在海因山 (Hain Mountain) 山坡上的亲切小镇,到处都是别墅和花园,到处都是盛开的灌木、玫瑰园和花坛。大自然似乎也认可了我们后来给那些美好日子起的名字:哥廷根玻尔节。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演讲。大厅里坐满了人,这位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站在讲台上,微微歪着头,嘴角挂着友好但又有些尴尬的微笑。他的身材足以说明他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夏日的阳光从敞开的窗户射进来。玻尔说话声音很轻,带有轻微的丹麦口音。当他解释他理论中的每个假设时,他用词非常小心,比索末菲平时小心得多。他精心构思的每一个句子都揭示了一长串潜在的思想和哲学思考,有所暗示但从未完全表达出来。我发现这种方法非常令人兴奋;他说的话似乎既新鲜,同时又不太新鲜。我们所有人都从索末菲那里学到了玻尔的理论,知道它是关于什么的,但玻尔自己说出来的话听起来完全不同。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的结论与其说是靠计算和论证,不如说是靠直觉和灵感,而且在哥廷根著名的数学学派面前,他很难证明自己的发现是正确的。每次演讲之后都是长时间的讨论,在第三次演讲结束时,我自己大胆地发表了批评意见。
玻尔一直在谈论克拉莫斯的贡献——也就是我被要求在索末菲的研讨会上演讲的主题——他的结论是,尽管克拉莫斯理论的基础仍未得到解释,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结果是正确的,总有一天会被实验证实。然后,我站起来,根据我们在慕尼黑的讨论,对克拉莫斯的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
玻尔一定认为我的评论是由于对他的原子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犹豫地回答,似乎对我的反对有点担心,在讨论结束时,他走到我跟前,邀请我那天下午和他一起去海因山散步。在那里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整个问题。
这次散步对我的科学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真正的科学生涯是从那天下午才开始的。沿着一条精心照料的山路,我们经过一家很受欢迎的咖啡馆,来到一个阳光普照的高处,从那里我们俯瞰着一座小小的大学城,那里耸立着圣约翰和圣雅各布教堂的尖顶,以及远处的莱内河谷。

图2 尼尔斯·玻尔(1885—1962)
玻尔开始了谈话。“今天早上,”他说,“你对克拉莫斯的工作表达了一些保留意见。我必须马上告诉你,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自己的立场,基本上,我比你想象地更同意你的观点。我很清楚,一个人对原子结构的断言是需要多么的谨慎。我最好先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个理论的历史。我的出发点根本不是认为原子是一个小规模的行星系统,因此受天文学定律的支配。我从来没把那当真过。我的出发点是物质的稳定性,从经典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纯粹的奇迹。”
“我所说的‘稳定性’是指同样的物质总是具有同样的性质,同样的晶体会重复出现,同样的化合物,等等。换句话说,即使由于外部影响而发生了许多变化,铁原子仍然是铁原子,具有与以前完全相同的性质。这不能用经典力学的原理来解释,如果原子类似于行星系统,那就当然不能解释了。显然,大自然有一种产生某种形式的倾向 (我使用的‘形式’这个词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 ,即使这些形式受到干扰或破坏,也能重新创造这些形式。你甚至可以想到生物学:生物体的稳定性,最复杂的形式的繁殖,这种最复杂的形式只能作为整体而存在。但在生物学中,我们处理的是高度复杂的结构,经受着某种特征的和临时的转变。我们不必在此问题逗留。让我们抓住在物理和化学中研究的更简单的形式。均匀固体物质的存在取决于原子的稳定性;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充满某种气体的电子管总是会发出同样颜色的光,一个具有完全相同线条的光谱。所有这些,远非不言而喻,根据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无法解释的。而根据牛顿物理学的基本原理,所有效果都有精确确定的原因,一个现象或过程的当前状态完全由它之前的状态决定。当我刚开始研究原子物理学时,这一事实曾使我非常不安”。
“如果过去几十年的实验没有给整个问题带来新的启示,物质稳定性的奇迹可能会被忽视更长时间。你知道,普朗克发现原子系统的能量是不连续变化的;当这样的系统释放能量时,它会通过具有特定能量值的某些状态来释放能量。我自己后来为它们创造了‘稳态’这个词。接下来是卢瑟福对原子结构的重要研究。正是在卢瑟福的曼彻斯特实验室里,我第一次熟悉了相关的问题。那时候,我比你今天大不了多少,我不停地问卢瑟福一些很长的问题。物理学家们刚刚开始仔细研究发光现象,忙着测定各种化学元素的特征光谱线;不用说,化学家们也提供了大量关于原子行为的信息。我有幸近距离地目睹了这些发展,自然使我想知道这一切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我试图提出的理论只不过是为了建立这种联系”。
“现在,这确实是一项无望的任务,与物理学家通常处理的任务大不相同。因为在所有以前的物理学中,或者在任何其他科学分支中,你总是可以试图通过将一个新现象归结为已知的现象或定律来解释它。然而,在原子物理学中,所有先前的概念都被证明是不够的。我们从物质的稳定性得知,牛顿物理学不适用于原子内部;它最多只能偶尔给我们提供一点指引。由此可见,对于原子的结构可能不会有描述性的理解;因为所有这些理解都必须以经典概念为基础,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概念已不再适用。你看,任何试图发展这种理论的人都是在做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想谈谈原子的结构,但缺乏一种能够使我们自己理解的语言。我们就像一个水手,被困在一个遥远的岛屿上,那里的条件与他所知道的完全不同,更糟糕的是,当地人说着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他只是简单地想让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但没有办法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理论不能用通常严格的语词的科学意义来“解释”任何事情。它所能期待做到的就是揭示其中的联系,其余的就让我们尽我们所能去摸索。这正是克拉莫斯的计算想要做到的;也许我在演讲中没有充分强调这一点。如果要做更多的事情,以我们目前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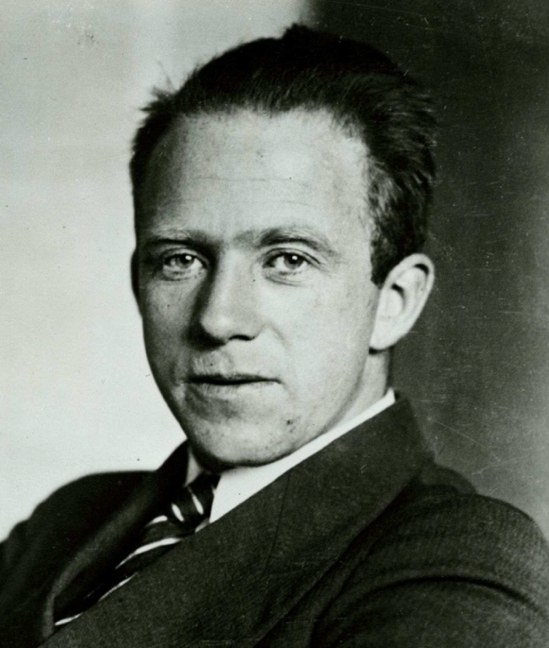
图3 沃纳·海森伯(1901—1976)
从玻尔的话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对我们所表示的一切怀疑都很熟悉。但为了确保我理解了他的意思,我问道:“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那么你在过去几次演讲中提出并证明的所有原子模型的意义何在?你到底想用它们来证明什么?”
“这些模型,”玻尔回答说,“是从实验中推导出来的,或者假如你更倾向于这样说,猜测出来的,而不是从理论计算中推导出来的。我希望它们也能描述原子的结构,但只是尽可能地用经典物理学的描述语言来描述。我们必须清楚,当涉及到原子时,语言只能像诗歌一样使用。诗人也一样,更关心创造形象和建立精神联系,而不是描述事实。”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才能取得进展呢?毕竟,物理学应该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也许可能的是,随着新实验的每一次出现,量子理论的悖论,那些反映物质稳定性的难以理解的特征,会变得更加尖锐。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只能希望,在适当的时候,新的概念将会出现,这些新概念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帮助我们掌握原子中这些难以形容的过程。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玻尔的话使我想起了我们在施塔恩贝格湖 (Lake Starnberg) 附近散步时罗伯特的评论,他说原子不是“东西”。尽管玻尔相信他知道关于原子内部结构的许多细节,但他并不把原子壳层中的电子看作是“东西”,无论如何,他并不把它们看作是与位置、速度、能量等概念一并起作用的经典物理学意义上的东西。因此,我问他:“如果原子的内部结构像你说的那样只是接近于描述性的说明,如果我们真的缺乏一种处理它的语言,我们怎么能希望理解原子呢?”
玻尔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想我们也许能做到。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不得不了解‘理解’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我们走了一小段路,来到了海因山的山顶,来到了著名的KerrInn,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自古以来人们通常会从这里返回。我们现在也向低地走去,这次是向南走,俯视着早已并入哥廷根镇的莱内河谷的山丘、树林和村庄。
“我们已经讨论了那么多困难的问题,”玻尔继续说,“我已经告诉过你我自己是如何开始从事这整个事情的;但我对你一无所知。你看起来很年轻。从你的问题来看,你似乎是从原子理论开始的,然后再去看正统的物理学。索末菲一定在你很小的时候就把你带进了这个冒险的原子世界。一定要告诉我这件事,还要告诉我你在战争中做了些什么。”
我承认,当时我才20岁,才上大学的第四个学期,对普通物理确实知之甚少。我继续跟他讲起索末菲的课,在他的课上,我特别被量子理论的神秘、无法解释的特点所吸引。我补充说,我太年轻了,不能参军,但我父亲曾作为预备役军官在法国作战,我一直很担心他。1916年,他负伤,被遣送回国。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我在下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做农场工人,以维持生计。不然的话,我可能已经被战争所用了。
“我想多听听你的意见,”玻尔说,“多了解一下你们国家的情况,我对这些情况所知甚少。关于青年运动,我从哥廷根的同事那里听到了很多。你一定要到哥本哈根来看看我们;也许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待一个学期,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物理。然后我会带你参观我们的小国家,告诉你它的历史。”
当我们接近城镇边缘时,话题转向了哥廷根的顶尖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马克斯·玻恩、詹姆斯·弗兰克、理查德·柯朗和大卫·希尔伯特,他们都是我刚刚认识的人。玻尔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去做部分研究。突然间,未来看起来充满了希望和新的可能,在看到玻尔回去后,我在回家的路上给自己画上了最辉煌的色彩。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